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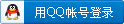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本帖最后由 南阳姚文书 于 2013-1-29 16:50 编辑
: c8 G- y+ t/ I( J# W" ^2 T$ V
$ U( U" D, v$ V* V3 Y I, z: r我的父亲母亲 一 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二十年来,兄弟五个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子欲养而亲不在”的痛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父亲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教师。1950年从内乡张集简师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去,足迹踏遍瓦亭、乍曲、师岗的山山水水——山南、药山、春景、东坡、陈营、红庙、双堰、南庄、魏营、孙岗、庵沟、山峰, 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无不印证着父亲的教学轨迹。父亲的墓碑上,我用“奉书敬业、贫而乐道、勤谨尽责,德铸师魂”来总结,一点儿也不为过。父亲从事工作的第一站是瓦亭。素有内乡“小西藏”之称的瓦亭乡山南村,与淅川接壤,人口不足四百,却有七个自然村落;人均不到一亩地,大多在山间石缝中,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地下水位很低,打不出水井,村民吃水都是靠村边池塘中积存的雨水;交通不便,到乡镇赶集要翻山越岭,徒步二十几里;靠山住,却没有柴烧锅,石头多,却没有利用价值,多年之前一直没有架电,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学校座落在村子对面的山坡上,生活条件比村里更差,没有电不说,吃水也要到村边池塘中去提,由于村民素质不高,放羊娃赶着羊也来饮水,所以羊粪和草芥是常见之物。就在这样的教学生活环境下,父亲在这里生活工作了多年,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记得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大概是1970年前后的一个春节,父亲到山南去,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无不欢欣雀跃,作为远离尘世的小山村唯一一个“公家人”、大先生,一个比自己年轻却又是老师的人,都以能够请到父亲吃饭为荣,农民们拿出陈酿老酒招待父亲。那都是积攒了一年,平时舍不得喝的黄酒。好像是排好了队似的,一家接着一家,从早上喝到晚上,一天、两天、三天......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酒,没有想到,喝了半碗就醉了,头晕目眩,在一个村民家里睡了一天一夜,第一尝到了醉酒的滋味,也感受到父亲得到了超规格礼遇。1972年秋天,父亲已经调离山南了,山南村的队长为了接济父亲,特意在山坡上划了一块荒草地,父亲领着大哥、二哥和我,一块儿去割荒当柴烧。在那缺吃少穿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份很大的帮助。当时我只有六岁,说是去干活,只能算添乱,可也再次领略了父亲在当地人心目中的份量。2007年夏天,父亲去世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我再次徙步翻越山梁,踏上山南这块凝聚了父辈心血的热土,看到似曾相识相识的学校、池塘、房舍,看到村民们已经陌生的笑脸,仍然能够感受到父亲当年的艰辛:每周从家里徙步往返六十里、一个人在这远离村庄学校的孤独、忍饥挨饿食不裹腹的日子。村民们用美酒招待我这位老师的儿子,大家第一杯酒集体献给长眠地下的父亲——父亲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父亲一生勤恳敬业、踏实做事。以力推人才为己任。在1976年以前实行推荐上大学的年代,当时父亲在乍曲陈营教学,连续二年,父亲推荐了本校青年教师陈金闯、许玉兰上了大学,改变了他们个人一生的命运,二人感激涕零、没齿难忘。父亲一生一线教学四十二载,育人无数,桃李盈枝,乍曲境内许多人都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性情耿直,踏实干事,不善于投机钻营。与他一块儿工作过的刘书章、时海法等老师,升任乡教育办公室主任后,手握工作调动的大权,父亲从来没有因为个人关系去走后门,把自己调动距离老家近点的学校,而是依然如故,根据组织的安排,让上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反而主动替领导着想,到其他老师不愿意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最明显的标志是离家越来越远了——南庄、魏营、红庙等校,离家都在十几里以上。父亲以教书育人为神圣使命,办公室经常挂着自己书写的座右铭——“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由于母亲常年疾病缠身,我及老四身体素质也较差,家里农活较重,父亲虽受拖累,却没有丝毫耽误教学工作。记得在陈营教学时期,有一段时间,母亲病情严重,父亲往往是请了医生、抓了汤药,安排好家里,赶紧去学校。有一天,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让不到六岁的我去远在三里外的大队部打电话,当我打完电话(当然是大队干部代劳)回到家里时,父亲不仅从学校赶了回来,而且请来了医生。小时候,我的体质较弱,经常发烧,甚至昏厥,有一次肚子疼得厉害,父亲从学校赶回来后立即背上我就向卫生院跑,到乍曲(老街)卫生院时累瘫在地上,使出浑身力气喊“救命”,引起医生重视,使我得到迅速救治。 父亲精心培育五个孩子成才,经常鼓励孩子们树立理想,要有所追求。他经常念叨,希望每个人各有所长,老大当军官、老二艺术家、老三当医生、老四当司机、老五营业员(当时吃香的几个工作:白大挂、方向盘、绿军装、营业员),唯独没有想过让哪一个让孩子当老师,可见他对教师这一行业辛苦程度的认知。对每个孩子的特长,因材施教,分别对待。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尖子生都集中在魏营学校,父亲利用到县里开会的机会,给我买了一本《中学语文词汇》,对我的语文学习帮助很大。生活上关心,记得有一天,在南庄教学的父亲,赶上村里杀猪,割了半斤大肉,给我送来。当时猪肉是一个稀罕物,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当时我在魏营住校,自己做饭,从来没有炒过肉,好像是丢在饭锅里煮熟了来吃的。在我1996年考上农业大学的时候,父亲十分自豪,逢人就说。当时村里有人不理解“学农业怎么还要上大学,祖祖辈辈没有上大学,庄稼不也种得好好的?”父亲不与他们计较,一笑了之。当时民间有一种说法:考上大学穿皮鞋,回家种地穿草鞋。父亲为了鼓励我,特意到师岗街花了半月工资(二十元),给我订制了一双皮鞋,那双鞋一直穿到我上班以后。 父亲热心为乡邻办事。由于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全村的对联几乎都由他包了,一年春节期间,总要忙上两三天的。凡是大家有要求的,一律来者不拒,有的家庭没有识字的不会贴对联,他写好后还要帮助人家贴上。村里有家孩子调皮,不肯正经上学,父亲就带他到自己任教的学校去,精心辅导。 父亲一年到头两头忙,一头忙事业,一头忙家庭。全家孩子都要上学,家中劳动力少,只有母亲一人出工,干了一天活,只能记7分(男劳动力10分),造成年年缺粮,父亲一年的工资收入有一半要交给队里买粮食了,父亲总不气馁,始终以乐观的态度对待。1970年与爷奶分开单独生活之后,父亲自筹木料,自己脱坯,找人打墙,盖起了三间屋架房,使一家人第一次有了宽敞的安身之地。考虑到孩子多的实际,之后的十余年间,父亲脱坯盖了两间偏房,并先后到庵沟、北沟炸山拉石,积累建房材料。1985年,孩子们大了,三间主房住着已经显得拥挤,父亲铆足了劲,把垒好的院墙扒了,硬是把村子西边的污水坑填了,建了三间砖屋。父亲一生注重栽树,改善生态,营造生活小环境。根据杨树易成活、生长快、木材好的特点,在门前广植杨树,目前门前的杨树已经不小了。既能纳凉,又能成材,一举两得。同时在院子里种了枣树和黑子树,把小院子整理得生机盎然。寒暑假时间,是全家最忙碌的时候,一年两茬庄稼,种子、化肥、种植、收获.......样样都要操心,特别是没有机械,没有哪一样农活是轻松的。尤其是割麦季节,最是紧张,一镰一镰割下来,打成捆,装车运到场里,打晒贮藏,一季下来,人们都要瘦好几斤;收秋季节,刨红薯,切薯片,凉晒收藏,最怕阴雨天气,半夜睡觉都得睁只眼睛,一旦发现有雨,全家立刻起身,抓紧把半干的薯片集中起来,第二天晴了,再分开摆放,直到凉干。一张小小的薯片,不止让人摆弄了多少次。父亲对此从未厌烦过、抱怨过。大学期间,有一次写信,父亲提到:“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庄稼活能干多少是多少吧。”其中包涵了诸多辛劳、诸多无奈。 父亲一生没有走出河南。只有一次郑州之行,还留下了诸多遗憾。1986年我考上了河南农业大学,父母相约一块儿去郑州看看,终于在1997年的春天成行,这是父母出过的唯一一次远门。在郑州市区跑了两天,住了一宿,无非是逛逛街、看看商场,没有舍得买什么东西。好在我借了一部120相机,虽说落后,毕竟留下了几张黑白照片。第二天说是去看刚刚建成的黄河大桥,从紫荆山百货大楼到花园路坐九路车,谁知等了半天,竟没有一辆车来,母亲怕我作难,就说算了。父亲幽幽地说:“不到黄河心不死啊,呵呵!” 父亲一生心态平和,从未过高要求。我1990年大学毕业之际,当时有两个好的选择:一是留在郑州编《河南农业》杂志;二是去洛阳市二商局下属单位工作。征求父亲意见,父亲说:“回来吧,我看在县城工作就不错。”当我揣着派遣证回到内乡,父亲与我蹲在县畜牧局对面好久好久,父亲说:“能在这儿上班,值了。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工作啊!”没有想到,两年之后,父亲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 父亲一生俭朴,唯一的奢侈品,也是工作的必需品,就是年轻时花了一百多元买的一块瑞士手表,父亲戴了几十年,到老也不曾换掉。可惜的是,已经老的不成样子的这块手表,竟被人偷了。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到走时工资也才210元,最后的丧葬费也为孩子上大学交了学费,可是父亲却培养了五个孩子全部成才,老大职级至县团级,老二、老三也都是正科级(通常县里称的局级),老四、老五是高级教师,更重要的是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如今子孙满堂,虽说分散在各地,可也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甚至买了小轿车,看到这些,父亲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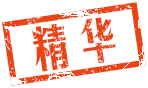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