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姚维侃 于 2015-9-19 16:56 编辑 1 b+ }! J% w$ h
4 ?1 _$ f' g8 K* T) [) J
建中宗亲的怀念老师的帖子,也激荡起对我的小学老师记忆的细波微澜。我在网易博客里写过我的几位老师,就把它转发到这里吧,以期博得各位宗亲一笑。 小学的老师除了我最敬爱的沈老师,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万英梅老师,胡阳春老师,胡兴新老师,还有一个头上有一撮白头发的张老师,已经记不起确切的姓名了。还有一个尚静生老师。那时校长是江思尧;主任是张春茂,这位主任论起来我得叫他姨父的,他的妻子也是钟鸣泉栏缪家的,他的岳父和我的外公是同胞兄弟。可那时他并不和我家打交道,因为我家成分高,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阵线吧。 先说万英梅老师吧,她教我们的算术,挺严厉的,她的教鞭可是常常和一些人的脑袋“亲密接触”的。大头宝宝(一个长着很大的头且又满头秃疮的总是欺负我的小学同学)就经常挨打,有时还会敲破“鸡屎”痂流血。还有一个全班个头最大的陈学堂也常常挨打。但万老师从来没有打过我,因为我在班里是小不点儿,却是学习最好的。她打的多是成绩差还调皮的。二年级时,万英梅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是在她的手里入了少先队的。那时上学虽然也要在表格上填写家庭成分,但还没有后来那样左到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都要遭受歧视,所以我入少先队只是个年龄问题。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真是心情激动,那种幸福感,那种认真劲,估计后来那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多年的右派得到平反时或可以和我相比。结婚后,和妻说起自己的学习经历,就谈起了万老师,没想到万老师也是妻的老师,而且还相当熟稔,万老师的养女叫“大夯”的,竟还和妻是同学。万老师的弟弟和妻的二哥又是战友。同在新桥这个小天地里,总有些这样那样的关系或联系也不奇怪。 胡阳春是对我特别好的又一个老师。他似乎是我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他上语文课时,班上很乱,轻易不发火的他真的恼怒了,把教鞭往讲台上狠狠一敲,一声喝斥,班上立时静了下来。他训斥了几句后,火气还没有完全平息,气呼呼地叫道:“现在谁来读一遍课文?”大家经这么一吓,谁也不敢举手,只有我举起了手,倒不是我没有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而是因为我一贯读书能读得声情并茂,朗读是我的强项,凡是老师叫学生读课文我从来都不会放弃争取这种机会。于是大家听我朗读课文,这时候全班寂静无声,只有我抑扬顿挫地读着,读完了,胡老师竟“扑哧”一声笑了,可能是憋不住而笑出来的,一不当心,把鼻涕笑了出来。这时班上又有点闹哄哄的了。 胡老师是一个脾气特别好的老师,可后来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再继续从教,而是去当了电影放映员了。 那时是升一年级换一个老师,到三年级时,教我的是胡兴新老师,有一只眼睛上有个鬏鬏,脸庞较大,说话带有当地圩区的口音。他可不喜欢我,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大喜欢我。在他的手里我可挨了不少批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宋伯罗为了打乒乓球的事闹起了矛盾,我们以墨汁为武器干了一仗,两人的脸上全抹得一塌糊涂,我们就这样被胡老师叫进了办公室狠兙了一顿。那时我已经是中队长了,胳膊上戴着两道杠的中队长标志呢,胡老师说:“你还是个中队长,你这是什么样吗?”惭愧!那时,真的很狼狈。 胡老师还是一个颇具艺术才能的老师,他能演奏好几门乐器,可能最擅长的是胡琴;学校里“六·一儿童节”排演节目绝对是由他来担纲的。排演节目总会抽到我的,那时一道排节目的有杨春娣,后来还当过我们的镇长呢!还有陈月英,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另有一个是能歌善舞的杨亚兰,都是长得挺漂亮的,要不说擅长文艺的老师都是最喜欢漂亮女孩的呢。 后来和胡老师还打过一些交道,一次是在初二时,1970年的元月,黄光明老师(另有专篇写这位给我印象和影响都最深的老师)带领我们去黄石溪学习革命烈士程庭财的英雄事迹——一个知青,为了搜集一个“叛徒”的材料,和一个“战友”一起掉进了雪坑里了,他把战友顶了上来,自己却牺牲在雪坑里了。现在可说不好了,说不定这个所谓“叛徒”其实是正遭人陷害的主,搜集材料云云,说不定正是在制造冤假错案也未可知。可烈士名份被确定下来后,估计是不好改动的了。从黄石溪回来,顺路去了九华山玩了一遭。那时那里的菩萨都被红卫兵造反派打得乱七八糟,堆叠得到处都是,也没时间看什么风景,就从贵池码头乘小轮船到横港了,当时,胡老师任教的小学就离横港不远,当时带队的我们的班主任黄光明老师可能早就知道的——他们是同事。这样就带我们去他那儿逗留了一会儿,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胡老师一眼就认出了我,而且明明白白地叫出了我的名字,着实让我感动了很久。 第二次打交道是很久以后了,1996年吧,胡老师的女儿胡亚敏师范毕业了,分配到我们学校任教了,他亲自送女儿来校,还提拎着一床和他那么清丽脱俗的女儿极不相衬的破被疙瘩。后来他还请当时的校长也是他的老战友江光有和我一起到他家搓了一顿。席间,两位老战友真是和谐亲密,不时还相互俏皮揶揄。江光有就说有一次大雨把学校的一间土墙房子淋倒了,大队的房后达书记去察看,却见胡老师在拉着胡琴,当即不留情面地说了胡老师一顿。胡老师见江揭他的短,也反唇相讥起来。那时我是教导主任,和校长王全胜有些关系紧张,他还承诺帮我和王缓和矛盾。其时,他早已是名扬市、县的县环保办公室主任了,早在我师范毕业后的1981年就改行了。现在是已经“退居二线”几年了吧。 还有就是尚静生老师了,他大大的个子,似乎有金牙。说话慢条斯理的,声音有点像女人。我那时可能在四年级,或是五年级,尚老师平时对我还算不错,但似乎也没什么对我特别的好。他留给我的印象还是兙我。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为学校食堂到朱冲拾柴禾,那时我在家里砍柴拾柴早已经是行家里手了,可能因为这次能在同学面前露一手,心里有点兴奋过头了,一路上有点忘乎所以,从管山那段铁道上走过时,铁路路基下面有一口井,不知是谁起的头,引起大家比赛看谁能把铁道上的道碴扔进井里。我当然也参加了,一路走,一路扔了好几个。在朱冲拾柴时,我和一个同学在炼硫磺的废窑上屙屎,不知被谁告发了,回到学校,尚静生把我好一顿兙!兙就兙吧,直到今天心里还对尚静生不留好印象的是,他不该上纲上线,说了一大堆什么“把剥削阶级家庭里的一些东西带到学校里来了”。我那时的家庭还叫“剥削阶级家庭”吗?往井里扔石头,在废硫磺窑上屙屎这些事能跟什么阶级理论联系起来吗?那时左的东西渐渐盛行起来了,尚静生大约是受了这些影响吧。但后来也没听尚老师入党做官的消息,大约他最终娶了一个地主成分的妻子毁了他的政治前途吧。 还有两位老师我怎么能把他给忘了呢!方月璋、胡永厚啊! 方月璋,大个头,桐城人,说着不打折扣的桐城话,可是清高傲慢,脾气暴躁。写得一手的仿宋体,在墙上写仿宋体标语,不用铅笔打草稿,先用小排笔写出外部轮廓,让别人将中间涂实就行。讲课有时就纵横捭阖,有机会也自吹自擂,但显然比其他老师显得有学问。脾气坏得可以,有一次,在课堂上,让徐志福(我们都叫他徐老五,他在家排行老五,家境贫寒;人很可怜老好)回答问题,但的确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方老师在课堂上就用桐城话骂道:“放你格大大屁!”这种脾气在那个年头,要是上三代及以下根正苗红,倒关系不大,顶多就是当不了官,可像方老师那样家庭成分也不好的话,那绝对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方老师先前就被打过右派,后来文革来了,他更是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踏上一万只脚”。有一年,他在学校办公室大门楣上写好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就被涂掉让朱世文再重写。看了那种情况,我就知道,调到凤凰山从教的他又一次被“打倒”了。方老师对我很好,不光是因为我作文写得好,也有可能掺杂了些同病相怜的成分在其中吧。 胡永厚,可是个人物。个头不大,说话最有特色,小声讲话时,是男声;大声讲话时尖锐得毫不逊色于女高音。他能用仿宋体写大标语,而且是先前写不过傲慢的朱世文,于是发奋,要在一个暑假里超过他,然后果真超过了朱世文。他还会园艺。他给我们上《农业常识课》,有几节课讲南瓜的培育,讲怎样温水浸种,怎样掐头打叉,怎样授粉,怎样养出比磨盘还大的南瓜,把我们吸引得恨不能立马就按他的方法试种起来。他又懂文艺,会排大型的群口词节目。由他导演的群口词节目似乎在当时是一种创新,因为我没有从别的宣传队的表演中看到过这种类型的节目。就是一群红卫兵小将,在台上每说一句台词,就变换一种动作,或高举拳头昂首挺胸,或马步下蹲,左手后摆右手胸前握拳屈肘,或作高举红旗状,或作怒斥“牛鬼蛇神”状……动作在说完台词后就凝固、亮相,和别的凝固的亮相配合组织成高低错落、威武雄壮的群体pose。那词也是胡老师编出的句句铿锵有力,字字刚劲豪迈,十分阳刚火暴的标语口号式的诗。胡永厚老师后来调回家乡太平乡中学当了几年校长。有一年去太平听课还见过他。 在我所有老师中,我最鄙视的就是朱世文了!尖下巴,匏牙齿,皮肤白晳,衣着整洁,头发总是光亮如新。文革时期当过学校革委会主任。先前看不惯他是他的色;后来恶心他是他的左。 他能写仿宋体标语,能画毛主席像,还爱打乒乓球,我上初中时他才来管山小学,那时,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小学从我们开始有了附设初中班,那时班里只有十七个人。他担任我们的化学课的教学,若是他讲课时把女同学讲笑了,那时他就像一只吃了兴奋剂的猴子,不只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连说话都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起来。虽然我们都知道他那时还没有对象,但也用不着那样啊! 当了革委会主任就抖起来了,像我这样的学生,即使学习成绩好,但家庭成分不好,在他那里是要另眼相看的。记忆最深的是有一次放学路上见了送队回来的他,我恭恭敬敬地敬个礼,叫一声“老师好!”可他只是点个头,鼻子里都不曾哼一声,眼睛都不朝我看一眼。要是别的学生叫,他会很客气的对他笑笑;要是漂亮女生,他就会眼睛笑成一条缝,满脸皱成一朵菊花了。 现在想来,他似乎从来没和我开过笑颜,也没有和我谈过一次话。永远只是冷冷的。和尚静生比起来,我更不喜欢朱世文:虽然尚静生也拿我的家庭成分说事,但那次我的确犯了错误,他批评我的行为是没有过错的,虽然有点上纲上线,说些对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沉重的话,但毕竟是不失公正;而朱世文不一样,我从来没有违逆过他,没有得罪过他,他是毫无理由地那样地对待一个不过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是很不公正的。所以,我当了老师后,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绝对要求自己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朱世文后来改行了,在朱村乡当过几年乡长,有一次在一起吃饭时,我见了他,却没有和他打一声招呼。这种人,懒得理他!后来又因为犯了什么错误,下台了,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了。这种人不成气候是合乎逻辑的。 # {, R0 t! y! ~; ]! `( 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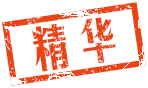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