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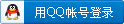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尧典》新解 金景芳 吕绍纲 窜三苗于三危, 《孟子·万章》、《大戴礼记·五帝德》窜皆作杀。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孟子·万章篇》窜作杀,杀非杀戮,即窜之假借字也。”又云:“经典窜、蔡、杀、四字同音通用,皆谓放流之也。”即蔡,《左传》昭公元年:“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经典释文》:“蔡,《说文》作。”“窜三苗于三危”,即把三苗流放到三危那个地方去。 三苗因何罪恶而遭流放,《尧典》无说。《左传》昭公元年言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论衡·恢国篇》:“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国。”关于三苗,《战国策·魏策一》吴起对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记·吴起传》作“左洞庭,右彭蠡”。《说苑·君道篇》、《韩诗外传》三皆同《魏策》。盖《吴起传》北向言之也。文山即汶山。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引张奇曰:“汶山太远,非在南,衡山亦不得在北。盖山为江之讹,而南北字上下误次也。”按,张说南北字上下误次,是也。《括地志》云:“衡山兼跨长沙、衡州二府之境,此三苗所居也。”《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云:“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是三苗活动范围相当广大,大致当今湘、鄂、赣三省。故马融云:“三苗,国名也。”(《经典释文》、《五帝本纪》集解引)所谓国,其实是一个部落。 又,《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注:“缙云,黄帝时官名。”《左传》昭公元年杜注:“三苗,饕餮,放三危者。”是文公十八年所云之饕餮,就是《尧典》“窜三苗于三危”之三苗。《左传》文公十八年叙述三苗罪状时,言“比之三凶”云云,视与另“三凶”有所不同。所言三苗之罪状重在物质上的贪欲,亦与“三凶”之在道德、精神上不良者异。是知三苗非华夏族。 所谓三苗,和经上文之共工、欢兜一样,既指一个具体的人即酋长,也指一个氏族或部落。流放的究竟仅止一人还是一个氏族或部落呢,古人未曾明言,但据《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既言“族”,则所流者定非酋长一人。 三危,《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西裔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杜注:“裔,远也。”是三危在西部远方某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又《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句下孔颖达疏云:“郑玄引《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地记》乃妄书,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注云:“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王鸣盛《尚书后案》:“三危自是西裔,但今鸟鼠之西,岷山之北,积石之南,大山亦多,不知当以何山为郑所指之古三危,阙疑可也。”按今甘肃敦煌东南有山名三危。是三危在汉之敦煌县,唐之沙州,今之敦煌市,可以确指,不必阙疑。 殛鲧于羽山。 殛字古人训释不一。《说文》歺部:“殛,殊也。《虞书》曰:‘殛鲧于羽山。’”段注:“殊谓死也。《广韵》曰:‘殊,陟输切。殊杀字也,从歹。歹,五割切。同殊。’据此知古殊杀字作殊,与诛责字作诛迥别矣。《周礼》‘八曰诛,以驭其过,禁杀戮,禁暴民’,野庐氏皆云诛之。此诛责也。《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此殊杀也。当各因文为训。”段注于许氏引《尧典》“殛鲧于羽山”句下又云:“此引经言假借也。殛本殊杀之名,故其字厕于殇、殂、殪、之间。《尧典》‘殛鲧’,则为‘极’之假借,非殊杀也。《左传》曰:‘流四凶族,投诸四裔。’刘向曰:‘舜有四放之罚。’屈原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尧长放鲧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郑志》答赵商曰:‘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寻此诸说,可得其实矣。”按段注之说极是。 《说文》殛字下引《尧典》“殛鲧于羽山”,段氏疑是后人所增入。“殛鲧”乃“极鲧”。这是有诸多文献可证的。《洪范》“鲧则殛死”,《多方》“我乃其大罚殛之”,《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经典释文》皆云:“殛本又作极。”又《周礼·大宰》八柄:“废以驭其罪。”郑玄注:“废犹放也。‘舜极鲧于羽山’是也。”此作“极鲧”,本叶林宗所抄宋本《经典释文》。宋本《释文》作“极,纪力反”。是郑玄所见《尚书》是作“极鲧”,不作“殛鲧”。段氏《古文尚书撰异》:“殛之所假借为极。极,穷也。《孟子》言‘极之于所往’是也。”又云:“刘向谓放、流、窜、殛为四放之罚。今浅学谓殛为杀,大误。”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亦云:“‘殛鲧于羽山’,今文与古文同,殛与流、放、窜同义,非诛杀也。伪孔不明殛义,并窜、放、流皆训诛矣。”《史记·五帝本纪》云:“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亦谓鲧因殛而死,殛非死刑。鲧被舜流放到羽山那个不毛之地,就死在那里。训殛为诛杀,于事理亦不合,处死本可随时随地,何须远至东方之羽山! 关于鲧其人其罪,《汉书·律历志》及《楚辞》王逸注引《世本·帝系》云:“颛顼五世而生鲧。”《玉篇》引同书云:“鲧生高密,是为禹。”《史记·夏本纪》云:“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两说差距甚大,一说鲧是颛顼之五世孙,一说是颛顼之子。比较而言,《史记》之说恐有误。《五帝本纪》与《夏本纪》说就不同。《夏本纪》说鲧是颛顼之子,黄帝之曾孙。而《五帝本纪》言颛顼之子只曰生穷蝉,未及鲧。鲧与帝喾同为黄帝之曾孙,而尧是帝喾之子,是鲧为尧之父辈。这多少有一点问题。问题更大的是《五帝本纪》明言舜之父是瞽叟,瞽叟之父是桥牛,桥牛之父是句望,句望之父是敬康,敬康之父是穷蝉,穷蝉之父是颛顼,即舜是颛顼之六代孙。根据《尔雅·释亲》规定的亲属称谓,舜是鲧的族昆孙,鲧是舜的高祖的族父。相距六代的两个人,怎么可能处在同时,一个人把另一个流放了呢!可见《史记》关于鲧世系的记载是混乱的。《尧典》和《左传》文公十八年关于舜殛鲧于羽山的记载既是历史的事实,则必须认定《夏本纪》之鲧是颛顼之子的说法为不可信,而《世本》“颛顼五世而生鲧”和《五帝本纪》舜是颛顼之六代孙的说法为近是。 最后,还有一个舜“殛鲧于羽山”发生在禹治水之前还是之后的问题。《郑志》:“答赵商云:鲧非诛死。鲧放居东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圣功,故尧兴之。若以为杀人父用其子,舜、禹何以忍乎!”是郑玄认为殛鲧在禹治水之后。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王肃云:“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后以鲧为无功殛之,是为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则禹之勤劳适足使父致殛。”是王氏以为殛鲧当在禹治水功成之前。按王说是,有文献可征,《洪范》:“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襄公二十一年:“鲧殛而禹兴。”杜注:“言不以父罪废其子。”《史记·夏本纪》:“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此四条材料皆言殛鲧在先而兴禹在后。 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指经上文所言之共工、欢兜、三苗、鲧,亦即《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言之穷奇、浑敦、饕餮、梼杌四凶族。罪字本作辠,秦时改作罪。《说文》辠字下云:“犯法也。”“四罪”二字在此句经文中不是一个词,指共工等四凶,而是两个词,“四”是四凶,“罪”指四凶伏罪,即受到应得的惩罚。或者说,舜给四凶治了罪,亦即经上文说的流、放、窜、殛。若释“四罪”为四凶即四个罪人,则这句话无谓语,读不通。等于说四个罪人而天下咸服,不成辞。汉人对此句经文的解释有对有不对。《汉书·鲍宣传》:“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汉书·息夫躬传》赞曰:“《书》放四罪。”皆以四罪当四凶,又在前另增一放字。经文无放字,《五帝本纪》前亦无放字。此增字以解经,不足取。《后汉书·杨震传》:“四凶流放,天下咸服。”《盐铁论·论诽篇》:“尧任鲧、欢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天下咸服。”《论衡·儒增篇》:“舜征有苗,四子服罪。”把“四”释为四凶、四子或具体指称鲧、欢兜等,把“罪”释为流放,释为放殛之以其罪,释为服罪,是对的。 “天下”,中国古代文献常用的词,其含义因历史时代不同而有变化。原始社会是血缘社会,在进入氏族制阶段之后,人们始终以氏族为单位,以部落为界限。人们的活动范围极小,氏族和部落就是他们视野中的天下,而后扩大到部落联盟,再扩大到部落联盟之外的其他部落联盟。尧舜时代已进入氏族社会的最后阶段,天下的范围应包括当时即被称为中国的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及四裔的异族部落。 “天下咸服”的“服”字应是《孟子·公孙丑上》“中心悦而诚服也”的服,不是《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服。服什么?伪孔传云:“皆服舜用刑当其罪。”是对的。舜流放共工等四凶,是以实际的行动实行了经上文说的“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和“唯刑之恤”的原则。虽有过错且造成后果但能改正的,赦免;坚持不改,顽固不化的人则必施刑。然而不施肉刑,更不诛杀,而是流放之于四裔。故天下皆心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 《说文》歺部殂字下云:“《虞书》‘勋乃殂’。”宋本《说文》盖如此。至《类篇》、《集韵》乃增放字,作“放勋乃殂”。至李仁甫乃增落字,作“放勋乃殂落”。《孟子》、《春秋繁露》、《帝王世纪》皆作“放勋乃殂落”。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认为今本古文《尚书》作“帝乃殂落”,可能是姚方兴本,未可为据。马、郑、王本当无落字。又,《尔雅·释诂》、《论衡·气寿篇》殂皆作徂。赵岐《孟子注》曰:“放勋,尧名。徂落,死也。”《尔雅·释诂》:“崩、薨、无禄、卒、徂、落、殪,死也。”这句话无论作勋,作放勋,作帝,也无论作殂,作殂落,作徂落,只是字形及用词上的差异,而句义并无实质性的不同,都是说尧死了。古人有今古文之争,我们知道就是了,不必继承他们的争论。 “二十有八载”,有,又。载,年。《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岁名。”孙炎云:“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禾谷一熟也。载取万物终而更始。”《孟子·万章上》引《尧典》此文作“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上作载,下作年。 关于二十八载的问题,《史记·五帝本纪》:“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引徐广云:“尧在位凡九十八年。”王鸣盛《尚书后案》云:“自‘厘降二女’以下至‘纳于大麓’,皆舜征庸事。自‘受终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摄位事。征庸二十载,摄位八载,时尧委政于舜,故总之云二十有八载。”又云:“《史记》与经合,郑说同此,的然可据者也。”按王说是。伪孔传说:“尧年十六即位,七十载求禅,试舜三载,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载尧死,寿一百一十七岁。”蔡沈《书集传》说略同。皆不足信据。 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史记·五帝本纪》以诂训代替经文,说:“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史记》的训释是正确的。百姓,古人多以下文“四海”对比而言,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谓“此经下文别言‘四海’,乃谓民间,则百姓自是群臣矣”。把“百姓”与“四海”相对照、区别而言,无疑是对的。但是以百姓为群臣,四海为民间,似不妥。此“百姓”应与经上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的“百姓”同义,而“四海”所指亦应同于经上文“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万邦”。尧既做到了“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在他死了,“九族”的哀痛自不待言,百姓与万邦(四海)悲痛之情是可以想见的。故云“如丧考妣”,“遏密八音”。 “百姓”何所指?所指是尧的部落联盟以内除尧的直近亲属即所谓九族以外的所有血缘团体中之所有的人,包括领导者和一般成员在内。说“百姓”指百官、群臣是不对的。因为当时社会由血缘团体为主;没有官员和民庶的划分。汉魏唐宋乃至清人释“百姓”为百官、群臣,是因为他们不知人们不是历来就划分为百官和民庶的,不知道尧舜时代是与后世根本不同的原始氏族社会。 “如丧考妣”的丧,就是死亡,死亡不言死或亡而言丧,有一定的意义。《白虎通·崩薨篇》:“丧者何谓也?丧者亡也。人死谓之丧何?言其丧亡不可复得见也。不直言死,称丧者何?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此说可资参考。考妣即父母,《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如丧考妣”这句话的蕴含,古人讲法不一,而以《孟子·万章上》“如丧考妣”句下赵岐注“思之如父母也”的解释最为恰当。 “三载”应独成句,上下皆断。“三载”是说哀思时间之长久,与后世周人之父丧君丧为子为臣者斩衰三年,母丧而父已先卒为子者齐衰三年的丧制是不一样的。三年之丧的礼制,尧舜时代尚未形成。说“三年”仅仅谓人们对尧之死曾经哀痛很久,是自然之感情,不是礼制的规定。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云:“周制丧考斩衰,丧妣齐衰。唐虞衰制则无文可考,此言‘如丧考妣三年’,止言其哀思之久,以见尧德之入人深,不必详其衰制。”江氏说大体得其实。但“三载”应断,既管经上文“如丧考妣”,亦管经下文“四海遏密八音”。 “四海”,上文曾言与经上文之“万邦”相当,相当是相当,然而不全同。《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包咸注云:“君子疏恶而友贤,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刘宝楠《论语正义》云:“注以经言四海,嫌有四夷荒远,故但举中国以九州言之。”《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是四海乃中国九州之外荒远处所居之夷狄戎蛮。尧死,夷狄戎蛮尚且“遏密八音”,华夏族人如何自可以想见。 八音,《周礼·春官·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玄注:“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白虎通·礼乐篇》:“八音者何谓也?《乐记》曰:土曰埙,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丝曰弦,石曰磬,金曰钟,木曰柷敔。此谓八音也。”《白虎通》之八音说与《大师》及郑注略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据《周礼·春官·籥章》“掌土鼓”,郑注引杜子春云“土鼓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以及《周语》伶州鸠言八音,以瓦易土等说,以为唐虞八音,盖鼓兼皮土二音,而无埙,埙作于周代。按孙氏之说不可从。据《中国音乐史图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出版)提供的考古材料,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埙。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江苏邳县小墩子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以及郑州二里岗早商遗址,都有陶埙出土。证明尧舜时代确已有了埙这种乐器。 不论八音为何,尧舜时夷狄戎蛮已有音乐是无可怀疑的。《白虎通·礼乐篇》:“东夷之乐曰朝离,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味,北夷之乐曰禁。”又:“王者制夷狄乐,不制夷狄礼。”是知古代夷狄戎蛮有乐而无礼。《尔雅·释诂》:“密,静也。”《孟子·万章上》“四海遏八音”句下赵岐注云:“遏,止也。密,无声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伪孔传:“遏,绝;密,静也。”经文的意思是,尧死了,本部落联盟内的人如同死了父母一样地哀痛,持续很长的时间,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内,荒远的夷狄戎蛮地区也都静悄悄地听不见乐声。《史记·五帝本纪》:“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是对经文极准确明通的训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颖达《尚书正义》引王肃云:“‘月正元日’犹言‘正月上日’,变文耳。”按王肃说是。月正即正月,元日即上日。 上日、元日是什么日?《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云:“上日,朔日也。”伪孔传亦云元日即上日,上日即朔日。孔疏更为解释说:“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长。元日还是上日。”亦谓上日、元日即朔日。王引之《经义述闻》驳之云:“上日、元日皆非谓朔日也。上日谓上旬吉日。当以叶氏、曾氏之说为是。(蔡沈《书集传》引叶氏曰:‘上日,上旬之日。’曾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类。’)元日,善日也,吉日也。《王制》:‘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正义》以元日为善日。《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卢植、蔡邕并曰:‘元,善也。’郑注曰:‘谓以上辛郊祭天。’上辛谓上旬之辛,不必在朔也。‘仲春,择元日命民社’,注曰:‘祀社日用甲。’甲日亦不必在朔也。古人格庙亦不必以朔日。”又云:“《太平御览》时序部十四引《尚书大传》曰:‘上日,元日。’亦谓上旬之善日,非谓朔日也。自张衡《东京赋》始以元日为朔日,而汉以前无之。”按王说是。元日即上日,上日即上旬之吉日、善日,不必是朔日。 格,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当是本作假。”《五帝本纪》“格于文祖”作“至于文祖”。《尔雅·释诂》:“格,至也。” “文祖”,郑玄以为明堂。《五帝本纪》明言“文祖者,尧大祖也”。伪孔传亦谓“尧文德之祖庙”。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尧本纪》曰:‘文祖者,尧大祖也。’太史公特用训诂之法为此语。尧大祖,盖谓黄帝。”按,诸说皆误。文祖即先祖,舜之先祖是颛顼。说见经上文解。 经上文言“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舜从尧那里受摄,为受摄而告庙。在尧曰终,终结他部落联盟首长的职务。在舜曰摄,摄行部落联盟首长的职务。此经文言“月正上日,舜格于文祖”,是说尧已死,舜为正式接任部落联盟首长的职务而告于祖庙。 这次告庙的时间在哪一年,是否有改元之事,这两个问题,古人看法不同。伪孔传以为舜即位告庙在服尧三年丧之后。此说有两点是成问题的,第一,蔡沈《书集传》云:“春秋国君皆以遭丧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庙而改元,孔氏云丧毕之明年,不知何所据也。”按蔡氏问之有理。第二,目前尚无充分材料证明尧舜时代有三年之丧。关于是否改元的问题,依郑玄说,尧正建丑,舜正建子,经文言“月正”就是改正亦即改元之意。王肃则认为“夏以上皆寅正”(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即尧舜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与夏代相同。也就是说,舜即位没有改元的问题。按王说是,尧、舜、禹、夏并无改元之事。郑说不可从。 询于四岳。 《尔雅·释诂》:“询,谋也。”“四岳”一词《尧典》多次提及,或言“咨四岳”,或言“询于四岳”。“四岳”是什么意思,古人众说纷纭,《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为四方诸侯。”郑玄注:“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伪孔传:“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韦昭注《国语》:“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为诸侯伯。”蔡沈《书集传》:“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究竟孰是,从《尧典》凡大事才“谋于四岳”或“咨四岳”来看,“四岳”非指一人,《汉书》的训释最得其实。“四岳”即四方之诸侯。不过“诸侯”一词是后世用语,尧舜时代所谓诸侯其实是指四面八方的众部落酋长而言。“咨四岳”是召开部落酋长会议,“询于四岳”也是召开部落酋长会议,同酋长们讨论、谋划重大问题的意思。 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辟,经文繁体字作闢。《说文》门部:“闢,开也。”《史记》闢作辟。达,今文《尚书》皆作通。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谓“古文《尚书》作聪”,“欧阳《尚书》亦作聪”,大小夏侯《尚书》作窗。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古文《尚书》本作囱。窗者囱之或字,窻又窗之俗体。聪又囱之同音。字作囱而或如字,或读为聪”。俞樾《群经平议》云:“四聪即四窗也。《释名·释宫室》曰:‘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是窗、聪声近而义通。辟四门,所以明四目也。达四窗,所以达四聪也。”又,“达四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引《后汉书·郅寿传》何敞言“辟四门,开四聪”,《班昭传》昭上疏云“辟四门而开四聪”,而按之曰:“何敞、班昭引皆作‘开’,则三家《尚书》必有或作‘开四聪’、‘开四窗’者。” 四门何所指?《诗·郑风·缁衣》孔疏引郑玄《尚书》注:“卿士之职,使为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门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国门,鲁有东门襄仲,宋有桐门右师,是后之取法于前也。”是郑玄以四门为国门。惠栋《明堂大道录》云:“明堂有四门,四方诸侯朝觐所入。”是惠氏以四门为明堂之四门。 四窗何所指?俞樾《群经平议》云:“古明堂之制,四旁为两夹,两夹皆有窗。”是俞氏以四窗为明堂之四窗。 今按,经文言辟四门,达四聪(或作窗),要在以之比喻舜广开贤路与言路,使上下通达而不杜塞,至于四门、四窗究竟是指什么四门什么四窗,其实并不重要。如果一定求寻确指,那么四目又是什么?《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辟四门,达四窗,以宾礼众贤。”《风俗通·十反篇》:“盖人君者辟门开窗,号咷博求。”《史记·五帝本纪》以训诂代经文,径作“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汉书·梅福传》福上书曰:“博览兼听,谋及疏贱,令深者不隐,远者不塞,所谓辟四门,明四目也。”《潜夫论·明暗篇》:“夫尧舜之治,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天下辐辏而圣无不昭,故共鲧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古人的这些理解虽不尽相同,但是大意一致,总谓贤路广开,言路广开也。 咨十有二牧。 《尔雅·释诂》咨、询皆训谋。有,又。十二牧,汉人皆释为州伯、州牧。《韩诗外传》卷六第十七章:“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窥远牧众也。”《说苑·君道篇》:“十二牧,方三人,出举远方之民。”《白虎通·封公侯篇》:“州伯何谓也?伯,长也。选举贤良使长一州,故谓之伯也。”又:“州有伯,唐虞谓之牧者何?尚质,使大夫往来牧视诸侯,故谓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书》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尧时十有二州也,以《禹贡》言九州也。”《汉书·朱博传》:“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叙引“十有二牧”,应劭曰:“牧,州牧也。”《礼记·王制》:“州有伯。”郑玄注:“殷之州长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蔡沈《书集传》:“牧,养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清人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按《礼记·王制》“州有伯”郑注后云:“是知此牧即州伯。‘十有二牧’者,十有二州之伯也。”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大传》曰:‘维元祀,巡狩四岳八伯。’疑四岳外,更置八伯。盖四方每方立一岳,每方又立二伯以佐岳,如周制一州立一侯,一州又立二伯以佐侯之比。四岳八伯合之即十二牧。” 以上诸说实质是两种意见,自汉宋以至于清代,多数人认为十二牧即十二州之牧。另一种意见如皮氏所说,四岳与八伯合之为十二牧。这两种说法都有问题,问题主要在于他们用后世周代和两汉的情况类比属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尧舜时代。尧舜时代的所谓十二州是自然形成的区域概念,与当时那场巨大的洪水有关。十二州不是行政区划,没有后世的所谓一州之牧或一州之伯。人们是按自然长成的氏族、部落等血缘团体组织起来的。对于一个人来说,氏族是唯一重要的,除了氏族之外,其他都不重要。对于一个氏族来说,部落是唯一重要的,除了部落之外,其他都不重要。部落始终是人们之间的界限,把人们区别开来的绝对不是行政区域。酋长的职务按照他们的传统办法在氏族、部落内部产生。酋长中的优秀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民主方式选到部落联盟中去担任公职,而不是相反地由部落联盟领导人向下委派部落的酋长。十二州牧之说与原始氏族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民主性原则是不相容的。经文说:“咨十有二牧”,不说“咨十有二州牧”,绝非出于偶然。牧这个词显然带有后世阶级社会的色彩,而实际上指的必是尧舜时代的部落酋长。“咨十有二牧”,是部落酋长会议的意思。十二这个数字与经上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一样,是泛称,不宜确指。 曰:“食哉惟时, 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引许宗彦云:“‘食哉唯时’四字不辞。考此经下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唯时亮天工’,文法正与此同,‘食哉’当为‘钦哉’之讹。篆文钦字偏旁与食字形近,文蚀其半,故讹作食耳。”认为“许说以经证经,极为精确”,故径改经文作钦。按许氏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证据实不充分,陈氏擅改经文的作法尤不足取。此句经文汉人无说,《史记·五帝本纪》引用《尧典》亦略去此句。伪孔传于“食”字如字作解云:“所重在于民食,唯当敬授民时。”蔡沈《书集传》亦云:“舜言足食之道唯在于不违农时也。”近人曾运乾《尚书正读》云:“食如艰食鲜食之食。时黎民阻饥,民食尤重,故首及焉。‘唯时’者,食为民本,而重农先在授时也。”以上三说同,曾说尤为明通可据。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据《方言》、《广雅·释诂》同训食为劝,《尔雅·释诂》训食为伪,伪即为也,以及《三国志·魏志·华佗传》“佗恃能厌食事”,食即为也,释经文“食哉”为“言劝使有为”。按孙说于训诂虽有据,而于经义难通,可略备一说而已。 $ q2 d) V1 p" s9 |4 X+ T% z9 k
. }; N3 v4 K8 _7 g" f) N( r3 }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