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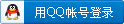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评近人对中国古史之讨论(节选) 张萌麟 顾氏因《诗》、《书》(除《尧典》、《皋陶谟》)无尧舜之称述,遂断定“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毫无疑义的”。吾于第一节已辨其谬矣。彼于论禹之来源时,又尝谓: 我们称禹为“夏禹”,正和称尧为“唐尧”,称舜为“虞舜”,一样无稽。《论语》上只言“尧舜”,不言“唐虞”,唐虞之号不知何自来。《左传》上所说的“陶唐氏,有虞氏”,乃夏代时的二国。……在《左传》上,舜没有姚姓,虞不言舜胤,尧没有唐号,唐亦不言尧后,或犹保存得一点唐虞二国的本相。 夏禹事前已辨明,兹不赘。且谓“《论语》上言尧舜而不言唐虞”,此全非事实。按《泰伯篇》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其言舜当唐虞之际,正与《尧典》相符。即此一言,已足尽摧顾氏之谬说。夏代之有陶唐有虞二国,毫不害尧之为唐帝,舜之为虞帝。夫刘邦之有天下也名汉,而刘袭之据粤也名南汉;李渊之有天下也名唐,而徐知诰之篡吴也名南唐,吾侪其可因南汉、南唐为后周之二国,遂谓汉、唐非刘邦、李渊之朝名乎?又吾侪既不能谓称尧舜必须言其为唐虞之帝,称唐虞必须言其为尧舜之后,然则又安能因《左传》之不言,遂谓其不如是乎?顾氏此处之谬,亦因误用默证。 尧舜与唐虞无关之说既不能成立,请进而论尧舜禹传授之史迹。关于此点,有当先决者二问题。(一)《尧典》、《皋陶谟》作于何时?(二)《论语·尧曰篇》首章是否为后人伪托?顾氏力言《尧典》、《皋陶谟》乃《论语》后之人所作,《尧曰》首章非《论语》原文。惟关于前者,顾氏至今尚未举出证据。(顾氏致钱玄同书中所举证据,已经刘掞藜氏证明其不能成立,见《读书杂志》第十一期。)关于后者,顾氏根据崔述之说。惟崔说当否,又成一问题。兹为斩除枝叶起见,先将《尧典》、《皋陶谟》及《论语·尧曰》首章搁置不谈,专从顾氏所举证据中观其所谓“尧舜的关系起于战国”之说能否成立。 (一)顾氏曰:“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吕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人所说,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 顾氏将《洪范》穿凿附会,刘掞藜氏已明辨之曰: 我们只要略略小心读《洪范》,便只看出不畀洪范九畴的是天,锡禹洪范九畴的也是天。鲧之殛死乃由彝伦攸,禹之嗣兴乃由鲧之殛死,并不是“殛鲧是天,兴禹亦是天”。这里又只言禹之嗣兴,并未说禹受天命而平水土。(《读书杂志》第十四期) 刘氏言甚当,无待予再赞一辞。次观《吕刑》云: 上帝监民,罔有馨香。……皇帝清问下民(《墨子·尚贤》中引《吕刑》,亦作皇帝清问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上帝不蠲。 此处前后均将“皇帝”与“上帝”对举,然则皇帝为非上帝而为人王可知。(郑康成谓皇帝指帝尧,当否且不论。)《吕刑》既明谓禹受命于人王,则所谓“他乃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之说乃不攻自破矣。水土为禹所平,九州为禹所画,而禹之迹所及又甚远,故以禹迹代表中国疆域。其所以不命舜域,其所以“将尧舜撇落一旁”者,正因舜未尝平水土,画九州,未尝有迹之故。 (二)顾氏曰:“《诗》、《书》中言禹的九处,全没有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了。就是伪作的《禹贡》,也是说‘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这是何等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赐玄圭’的话,正作如此解。)” 读者须注意:顾氏所谓“完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一语,实犯笼统之病。如何谓之“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如何谓之“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顾氏未尝道及只字。夫《诗》《书》中(除《尧典》、《皋陶谟》)无禹为尧舜臣之记载,此是事实,然亦未尝有禹非舜臣之反证或暗示。若因其言禹九条未尝谓禹为尧舜臣,遂断定禹非尧舜之臣,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诗》《书》(除《尧典》、《皋陶谟》外)非尧舜禹事迹之记录,而言禹亦无必说明其为尧舜臣之需要也。 《禹贡》乃叙述禹在各地治水之经历,何能将禹与尧舜之关系事实牵入。且治水非在朝廷咫尺间之事,周行天下,去虞帝不知几千里,若不能“独断独行,称心布置”,必恃请命而后动,则终其身不能疏一河矣。顾氏因其“独断独行,称心布置”,遂谓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人臣的意味,真所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一语,固未言锡圭受告者为尧,然亦未言其为上帝,安能增字解释,任情附会耶!皇甫谧乃惯造伪史之大家,《符瑞志》乃妖言之总集,而号称疑古之顾氏乃引据其语,吾未解何故。 (三)顾氏曰:“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无关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这可以见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按《论语》、《楚辞》并无尧舜与治水无关之证据或暗示。若因《论语》未尝言及尧舜与治水相关之事实,遂谓尧舜与治水无关,此又违反默证适用之限度。何也?《论语》、《楚辞》非尧舜事迹之记录,而言尧舜亦无其治水之关系之必要也。《左传》昭七年,言“尧殛鲧于羽山”,乃出诸郑子产之口。僖三十三年,言“舜之罪也殛鲧”,乃出诸臼季之口。二人历史智识之程度未必相同,其矛盾何足异。譬如有某学校考历史,一学生言明毅宗死于李自成之难,一言其为清兵所杀,吾人其亦谓“这可以见出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大家顾全不得的情形”乎?退一步言,上述二语非出诸子产、臼季之口,而为《左传》作者所附加,亦安能保其无因疏略而致误。且从逻辑上言之,凡两相矛盾之说,或有一谬,或两者俱谬,不能因其矛盾遂断定其两者皆虚也。 由此观之,顾氏谓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其所举证据皆不能成立。此外顾氏以此观念为基础而建筑之空中楼阁,自无劳吾人之拆毁矣。综合以上两章,可得一结论曰: 顾氏所谓“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其说不能成立。其所以致误之原因,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凿空附会。 (《古史辨》第二册,朴社,1930年)
9 {0 L5 z/ e, N( b7 X: U0 c/ U( y0 Z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