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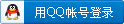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舜帝道德:中华文明传统与社会和谐 尤慎 一、基本认识 目前研讨舜帝及其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由于虞夏时代的考古材料缺乏,还只能倚重古文献,大家都是依据自己的认识来解读的。以下则是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认识。 中华文明的起源,其野蛮时代开始的标志是原始农业和制陶业的出现,其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则是文字体系和国家的出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我国原始农业和制陶业萌芽的历史年代距今大约有1万年。从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的原始栽培稻粒和陶釜看,其起源的时代可以认定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之际,远远要早于古史传说的炎帝神农时代。道县玉蟾岩栽培稻距今约12000年,炎帝神农时代距今约5000年,年代提早了7000来年。而距今6000~8000年的农业遗迹,如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北辛文化、贾湖文化、彭山头、八十垱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分布广泛,农业发展阶段已明显高于道县玉蟾岩水平,当然应有其更早的起源。因此,中华文明的远源不是5000年,而是10000年;不是中原一枝独秀,而是南北东西中百花齐放,有的地方可能比中原文明更早更发达。 可见,到距今约4200年的舜帝时代,湖南永州一带的农业文明已有了约8000年的历史,没有理由推测当时是非常蛮荒闭塞落后的地方,令古人望而却步。唐代刘知幾《史通·疑古》以永州荒远可怕为由质疑舜帝南巡九疑,今人或从之,显然是低估了江南文明,也低估了古人的活动能力。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我们赞同如下看法:三代及其以前的考古文化,既有明显的发展不均衡性和地域差异性,又往往具有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特征;既有虞夏商周统治政权的纵的承接关系,又有其部族先祖活动地域的横的平行关系。因此,中华文明起源总体上是多元的,但又不是孤立地各自发展,而是不断地融聚和扩散;不是各地域均衡同步发展,而是中原逐渐领先。到龙山文化时代,或者说五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开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而且中原华夏族及其文化的优势明显。这里,黄帝族的崛起与率先进入古国文明时代,正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起源向统一融合发展的关键和跨入新文明时代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帝时代中原已进入“一元化”为主的时代,也不是不可以的。 与此相应,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融合之后,中原及其附近的众多姓族或氏族在婚姻血缘上和文化上都已经不同程度的黄帝族化了,特别是其首领个人或王族,往往与一般平民有区别。这必然普遍形成了并日益扩大了华夏族来源于黄帝族的认同心理。当然,由于他们融入黄帝族的时间和程度不同,也可能某些泛黄帝族化的部族,在不同时期、不同支系中具有两种族属认同心理,即有时自认母系远祖而有别于狭义的黄帝族,有时又自认父系高祖属于广义的黄帝族。古籍多说华夏族皆来自黄帝族,主要是由此而来。至于其中存在的某些族属与世系问题,也是由此而来,当然也有传说失载的原因。这一点,目前考古学还很难证实,但语言文字学的推论确实言之有理,张光直先生认为:“‘民族’是因语言和文化特征来分类的。我们虽然不了解夏民族语言的详情,但是根据现有的关于夏代的资料,我们没有理由推测它与商、周语言有任何区别。”[1]黄帝族的直系夏王朝禅承虞舜政权,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推测五帝时代与夏代语言有多大的区别。 正是由于以上事实,所以司马迁将《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第一篇,这是继承了远古以来的华夏文明起源认识,主张“五帝”为华夏民族之祖,华夏文明之源。司马迁的说法,今人或嗤之以鼻,以为是违反常识的文明起源“一元论”,其实从古文献证据来说,从目前的考古认识来说,却不无道理。司马迁只是说到距今4500年的近源,并没说更早的远源;更重要的是,司马迁是说华夏文明的主流主体,而不是说全局全体。不能苛求司马迁对今天中国范围内的古代文明的渊源和全局能够认识清楚,其实我们自己至今也很不了解。因此,司马迁的说法,不是所谓的“一元论”,而主要是统一论。从发展观来看,多元统一论是辩证的,既不能否定多元起源,也不能否定统一趋势。误认古人的统一论为“一元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一元论”,是当今疑古派观念的一种主要弊端,必须破除。简单的疑古已经结束,重要的是找到新的有力证据,作出新的释古。我们认为,司马迁虽然并没有现代文明起源理论,但今人所关注的华夏文明要素,如城市都邑、兵器军队、宗教道德、礼仪祭祀、君王官制、税赋田地、语言文字、民族来源等,都基本涉及,应该说,司马迁已经具备感性认识中华主流文明起源的能力,的确很了不起。这就是说,司马迁的《五帝本纪》可信度较高,既基本符合华夏主体文明起源理论,也基本符合目前考古发现的实际。 关于五帝时代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的地位作用,现代的说法,谢宝笙先生具有代表性:“五帝时代是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之初,是中华民族远祖从元谋人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积累了一百多万年量的进化而取得的一次质的进化,这个质变非同小可,它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使中国人和世界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因此五帝时代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真正起源,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五千年。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时代,或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之前的文化,纵使有一些多元因素,但经过五帝时代的巨大历史实践和融合之后,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特色已完全建立起来。而彪炳后世的禅让事件,则在五帝文化的融合与形成中有着凸显的核心作用。”[2]强调中华文明的特色形成,是一个不错的论述角度。古人对此的认识则归结为“大道之行”或“明德”,强调的是道德。认为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道德文明,古人的概括是相当意味深长的。 五帝以来的道德传统对华夏民族及其文明,对华夏社会和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舜帝的道德典范的深远影响。《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着重记载的是黄帝和尧舜的德政,而尤以舜帝道德为主。文章对舜帝的世系、家庭、德行、德政作了较详细的记载,并高度赞颂地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一个“德”字,概括了舜帝一生的功绩;一个“皆”字,概括了舜帝对黄帝以来事业的全面完成;一个“始”字,概括了舜帝的开创性贡献对后代的深远影响。周先民先生认为:“如果把缔造中华、凝聚民族、发展文明看作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是由五帝的合力建设完成的。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阶段:(1)黄帝肇始奠基。(2)颛顼和喾添砖加瓦。(3)尧帝大力推进。(4)舜帝全面完成。”[3]舜帝全面完成的说法,其实就是太史公“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观点的现代说明和发挥。我们认为,五帝时代后期,华夏民族的强大及其文明传统的灿烂辉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一和谐的基本趋势,而正是这种社会统一和谐的历史趋势,又巩固发展了华夏民族的特色和华夏文明传统,这都与舜帝的道德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可以说,虞舜时期是华夏文明传统定型的关键时期,舜帝是华夏文明传统和社会统一和谐的奠基者之一。 二、舜帝促进了华夏民族的融和与认同意识 五帝时代最主要的矛盾是部族之间的矛盾,来源于资源的争夺、地位的竞争、文化的冲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文明先进部族对异族的战争和同化。促进华夏民族大融合的首先是黄帝,他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最后败炎帝于阪泉,擒杀蚩尤于涿鹿,基本上达到了中原的统一,组成了以黄族为核心,以黄炎夷联盟为主体的北方民族集团。败散的其他民族严重受挫,难以发展为较强的古国,文明进程明显落后。其中大江南北的苗蛮族势力较强,虽然严重受挫,但并没有被征服,于是形成了南北两大民族集团的对立。黄帝的疆域只能南至长江。至颛顼,势力范围扩大到南至于交趾。至尧帝时,天下大水又大旱,面临巨大危机艰难,三苗又趁机在江淮、荆州为乱,这说明南北民族矛盾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舜以前的古帝王尚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到了舜帝,这个最大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这是舜帝对中华民族融合凝聚的巨大贡献。由于天下水患,各部族都面临生存危机,减缓了部族间的矛盾,舜帝使用武力是适可而止的。他所打击的是破坏社会安定者,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舜帝亲征有苗,或命禹征有苗的记载,典籍中数见。另一方面,舜帝采取怀柔感化的政策,收到较好的效果。史载:“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这样,“舜却三苗,更易其俗”,使南方民族大量地融合到华夏民族之中,或渐渐地受到同化。当然还有一部分三苗人在继续抵抗,渐次向更南方退避。《帝王世纪》载:“(舜)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舜在使禹摄政后仍要亲征有苗,说明舜一生以平服三苗,实现南北民族统一为己任,死而后已,也说明三苗对态度强硬的夏禹心有不服,而对舜心有好感,舜出征容易成功,甚至可以不战而定。舜帝南巡并留葬江南,在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历史上是一件最值得注意的大事。自古以来,“舜迹”遍布南北各地,说明舜帝在南北各族人民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舜迹”在南方很多,流传甚广,这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舜帝受到南北民族的共同崇拜,说明华夏民族已明确形成了传统的民族认同心理和意识。 关于舜帝是否南巡崩于苍梧葬于九疑,至今争议不决。我们认为,舜帝陵在九疑乃是古今主流的看法,文献证据和考古证据都更为充分。2004年,九疑山玉琯岩发掘出舜帝陵庙遗址,规模宏大,有3万平方米。据专家学者考证,时代可追溯到东汉以前,可以与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相印证。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明确标出舜帝陵在九疑山,时间不晚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马王堆地形图上的舜陵其实还有更早的渊源。据《国语·吴语》:“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以不入。乃筑台于章华之上,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可见,舜帝陵在春秋时代即已存在,且其形制为楚章华台所仿造。马王堆地图上的舜陵标记为“帝舜”,楚人伍子胥也称为“帝舜”,名称相一致,应不是偶然的。由此可证,马王堆地形图上的舜陵至迟在春秋晚期以前已经存在。 舜帝对中华民族融合团结的巨大贡献还有一点,那就是进一步促进了华夏民族集团的内部亲善。这里涉及到舜帝是否华夏族的问题,有必要讨论一下。 据《史记》,舜为冀州人,为黄帝血脉后裔。而《孟子·离娄下》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赵岐注认为,孟子的原意是说舜帝和周文王是东夷地方和西夷地方的人,而不是说他们是东夷族人和西夷族人。他们只是一生活动在东方和西方而已。杨伯峻先生《孟子译注》的看法相同,他直译为“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则是东方人。文王生在岐周,死在毕郢,则是西方人。”古人论族属,必追溯其姓氏、祖先、世系,而不是只说其生死之地,所以赵岐和杨伯峻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 而且,《孟子·梁惠王下》三次提到周族先祖自别于夷狄,《孟子·滕文公上下》两次提到周公打击夷狄,并定性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都可以证明孟子并不认为周文王是西夷族人。那么,从孟子并列舜帝和周文王的句式特点看,孟子也不会认为舜帝是东夷之人。 周族先祖是华夏族人,迁到西方戎狄地域是迫不得已的,古籍有明确的材料。据《国语·周语上》,祭公谋父曰:“昔我先君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君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祭公谋父是周公之孙,他的说法说出了其中的原委,也显然代表了周人自己的民族认同心理。钱穆先生《西周地理考》据此考证周族起源于晋南,即临汾一带,后来才迁到陕西北。现代陕西考古发现证明:古代戎狄遗迹寺洼文化与先周文化地域相邻,但寺洼文化和姬周文化分属于不同的两种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明显高于周围的戎狄文化,属于中原文化,与《诗经》的说法相合,最合理的解释是周族并非来源于西北戎狄族。 许多人主张舜帝不出于黄帝族,最重要的理由是舜帝妻尧之二女,如果舜与尧同祖,有悖古礼。何光岳先生认为:“舜帝正因为入赘于黄帝、颛顼族的尧,为尧的女婿,所以舜的子孙便把尧、颛顼、黄帝当作祖宗来祭祀。所以说,舜是由东夷族融入炎黄族的。”[4]其实,春秋时期仍存在同族同姓通婚之事,远古同样会有。 不论如何,总之以舜帝和二妃的感召力,华夏族的亲和团结无疑会大大加强。舜帝受禅尧位,曾避丹朱,登帝位后,重用各族贤人,公正清明,必然会有力促进华夏族的团结。舜帝不传位于其子,而是传位于禹,这必然可以消弭分裂和争夺,有利于中原的稳定和安定。舜帝的一生,真可谓是民族和睦融聚的表率。后来夏居于中原,商来自东方,周来自西方,均以黄帝为华夏之祖,与舜帝的关系极大。 三、舜帝发展了华夏早期国家制度 我们认为,从黄帝称霸中原开始,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氏族部落联盟体开始发展为原始国家。据《五帝本纪》,具体标志有如下几点:(1)以师兵为营卫,即有了常设军队和卫戍部队。(2)有官职,如左右大监。(3)有都邑,在涿鹿之阿。(4)有宗教礼制,如封禅、推策、宝鼎之类。(5)有广大疆域,东至于海,西至于空峒,南至于江,北至于釜山。(6)有征伐不顺之权势。(7)有分封制度,如玄嚣降居江水,昌意降及若水。陈唯声先生曾从考古材料出发,比较了中西文明和国家的起源,认为“参照世界史上确定文明的通例,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应提前几百年,即上溯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5]。这个时代,在金属工具,城镇建筑、文字、墓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阶级分化等方面,均不逊色于国外其他文明中的早期国家。特别是年代相当于尧帝时代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考古研究结果大致可以印证古籍的说法并非虚构。 到了尧舜禹时代,中华古国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程度,而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舜帝。舜帝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1.设置了分工明确的官制和官吏考核制度 在尧帝以前,各类官职不明,重大事件都是召开四岳会议商定,临时指派某人去完成的。舜帝一方面保留了四岳会议的传统,一方面明确地设立有司居官相事,委托了22位大臣,并作了具体的分工安排。例如:伯禹为司空,平水土;弃为后稷,掌农事;契为司徒,掌五教;皋陶为士(又曰大理),掌五刑;倕为共工(又曰工师),掌手工之事;益为朕虞,掌山泽鸟兽;伯夷为秩宗,典三礼;夔为典乐,掌礼乐教化;龙为纳言,掌出入帝命和宾客。可以看出,农、林、工、礼、乐、刑等部门已经形成了系统,中央官制的雏形已确定下来了。以后夏商周乃至秦汉,大致上都是沿用这个系统,不过是有所增益、调整,改换了部分名称而已。 舜帝在任命这22人时,虽然也征求了四岳的意见,但没有任何人反对,显然已与尧帝时有所不同了,说明舜帝时君王集权上升。 舜帝不仅设置了系统官制,还创造了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尚书·尧典》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三年考核一次,三年决定升降奖罚,不仅合乎原始民主传统,又加强了君王和国家权力,实在是一个高明的创举。 2.扩大国土并划分政区 黄帝时的疆域已如上述,至颛顼,最大的发展是南方达到了交趾。其后帝喾和尧帝都有所扩大。舜使禹治水,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大大有利于舜帝开拓疆土。这时,国土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舜在禹定九州的基础上,划定十二州,委任十二州牧治理地方。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又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看来十二州牧可能有八恺八元在内,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这十二州牧可能有的就是各地的部落首领,但性质上已是行政区首长,是按地域来治理的,而不再是氏族部落以种姓来治理其领地。十二州中心为冀州,这是各族凝聚统一的表现。十二州的划分,是舜帝的重大贡献,一直影响到中华五千年,后来的郡县制、省县制都是在十二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 3.制定和颁布了刑法 刑法作为一种惩罚报复手段,在原始氏族之内和之间早就存在了。但将它制度化,形成条律,并由专职官员审理,却是国家成熟时才能产生。尧以前刑律未见详细记载,至舜帝才有系统的记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这段文字虽然很简短,意义却十分深刻久远。第一,“象”者,刻画也。故知舜帝已刻刑律于器物,使民知所惩戒。春秋时代,郑铸刑书,晋铸刑鼎,郑又著竹刑,孔子大力反对,现代历史学家则誉为大事,其实早在舜帝时就已经开了先例。第二,官吏犯罪,要施鞭刑。三代有刑不上大夫之说,那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度消失太久时的产物。第三,过失小罪,可赦,而怙恶不悛,当刑。注意有所区别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自古以来都接受了这种思想。第四,流宥五刑,金作赎刑,体现了仁慈宽刑的精神。第五,慎刑原则,“钦者”,敬也;“恤”者,慎也。用刑唯慎,以免滥刑暴政。刑律颁布后,舜命皋陶作士,并指示:“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维明克允。”可见舜作象刑,主要是针对蛮夷的,但很注意掌握一定的尺度分寸,以公正廉明来使人心服。舜帝罚“四罪”(三苗、共工、兜、鲧),流“四凶”(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其中既有蛮夷,又有黄帝族人,还有东夷族人,既有高官诸侯,又有不肖子弟,可见舜帝确实做到了“维明克允”,誉为中国刑法学之父亦不为过。 4.确立了帝王巡狩制度 黄帝以来的古帝王,虽然也有巡行边陲,祭祀名山大川的记载,但并未形成制度。到舜帝,每岁二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每年巡狩东南北方一遍,与春夏秋冬四季结合,这样的巡狩每五年要进行一次。目的一是祈求四方神灵赐福,二是了解各地实情,三是与各地核对历日和度量衡,促进华夏统一,四是安抚各地,融洽关系。因此,帝王巡狩制度对巩固国家政权很有必要。而古代巡狩四方是很劳累的,只有勤政忧民的帝王才能坚持下来。值得注意的是,舜帝巡狩每一处,都要“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看来最早开始统一历法、度量衡的,并不是秦始皇,而是舜帝。 5.实行了帝位禅让制 舜帝晚年,黄河水患已经平定,社会动乱已经得到治理,与尧帝时处于艰难时期大不一样,此时舜帝能自觉禅让帝位,当然是道德最为高尚。 产生于战国中期的逼篡说,实不足信,第一是文献证据不足。逼篡说最早见于战国中期的《竹书纪年》和《韩非子》。《竹书纪年》下葬于魏襄王二十年,大约与《郭店楚简》同时。而春秋及其以前的记载均与禅让说相合,《左传》文公十八年提到舜帝有大功二十,得到天下拥戴而为天子,这已符合尧舜禅让的前提之一;《国语·楚语上》说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皆是父有元德而有奸子,这已符合禅让帝位的前提之二;又春秋以前许多名人众口一词认为舜帝道德高尚,这又排除了舜帝逼篡的可能。所以后来儒墨盛赞的禅让说更符合古来传说的原貌。再说,《韩非子》是引用“奸臣”之语,奸人伪造的迹象很明显,韩非子本人的态度暧昧。可见逼篡说出现较晚,只是战国中期从法家起源地三晋一带流传的,而此前的春秋晋国名大夫,如臼季、吕相、师旷、范宣子、蔡墨等人,都没有透露逼篡说的迹象,而是高度赞扬舜帝的道德高尚。我们认为,《竹书纪年》追记的远古历史同样明显具有战国时代色彩,凡是上古贤德君相常被否定,这就未必全可信从。例如,其中关于伊尹篡位而被太甲所杀的记载,与《孟子·万章上》的说法相反,《竹书纪年》的说法已被甲骨文所否定。 第二,否认禅让说的理论根据片面。据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和上海博物馆竹简《容成氏》,禅让是远古社会形成的传统,在黄帝族进入古国王朝时代后,仍是很难改变的权威观念和很难对抗的保守势力。直至千年之后,周武王凭武力夺取天下,仍然深深感到这种传统势力的压力,全力为其天命辩护,并分封古代帝王后裔以示正统。难怪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各朝各代,禅让之事始终被人怀念和重提,这并非完全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在广大群众心里,它代表了天下最大的公正和最高的道德,是避免部族方国之间矛盾激化的有效方式,是华夏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和谐的标志。所以孔子在《礼记·礼运》中将禅让视为“大道”的核心,作为“大同”时代和“小康”时代的分界线。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必然加剧了暴力和杀戮,但这只是总体的趋势,具体事件不可能一概如此,而且也必然引发民众的愤慨和对禅让的赞扬。尧舜的禅让有其历史传统的必然性和深刻的社会基础,决不能以阶级社会发展趋势简单地予以否定。具体到不同的君相,禅位者有之,夺位者有之,半禅半夺者亦有之,不可一概而论,不能轻易否定大量古文献的记载。 四、舜帝奠定了华夏民族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道德 在氏族社会,人们都是按血缘关系共同生活的,最早的人伦关系和伦理观念当然要以血亲关系为核心和基础。对子女来说,孝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否则以族长为中心的氏族根本无法代代维持生存下去;到了黄帝时代,即在宗法体系基础上形成早期国家的时候,第一美德仍然是孝。因此,孝行成为考察贤能的一个首要标准。尧帝选择舜帝时,第一好感就是孝,毫不犹豫地选定舜为女婿,使他具备了接任帝位的最佳资格。而四岳推举舜,首先提到的就是孝,看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孝子”就是舜。 在“父顽,母嚚,弟傲”家庭中,舜帝“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其艰辛苦楚远远超过了一般人,所以《二十四孝图》将舜帝列为第一,而敦煌变文中则称舜为“苦孝子”。舜帝的许多故事,人们都渐渐淡忘了,但他的孝行世世代代被当作典范而流传下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影响最为深远。 孝的本质,从思想情感上说,就是爱父母。在氏族时代,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自然地从爱父母推广到爱一切族人、一切人,这就是仁爱。到氏族解体,国家诞生后,私有、贪欲、诈谋、盗窃、乱贼日盛,仁爱之心日益淡薄,故孟夫子要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舜帝对其父母弟妹的孝悌,这是仁。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当地之人能在他的仁义言行影响下,让畔,让居,器牢而无欺。舜帝所到之处,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感召力之大,实不待言,这也是仁。舜帝摄政之后,兴利除弊,勤政野死,这也是仁。舜设象刑,使民知畏,慎刑宽宥,这又是仁。舜除“四罪”、“四凶”,为国为民除害,这实际上也是仁。舜受禅帝位,勇承大任,而又急流勇退,这还是仁。舜对三苗修文德以来之,不得已而用武,这同样还是仁。舜帝自古以来深受人民爱戴,因为他实在是个仁义之君。仁孝合一,后来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 舜帝不仅亲为表率,努力行孝施仁,而且还大力开展教化,选拔专职官员来主管道德教化,或进行配合。舜帝是个著名的孝子,二十以孝闻,尧帝当然首先委任他“慎和五典”,即司徒之职,结果“五典能从”。舜帝践天子位后,“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又委任契为司徒,敬敷五教。而以伯夷为秩宗(郑玄曰:“主次秩尊卑。”),夔为典乐,教稚子,皋陶为士,使礼、乐、刑与教化互相配合,大力促进了古代道德伦理观念的制度化。 总之,我国古代的伦理观念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的核心是孝。忠是孝的推广,仁是孝的实质,这些都集中体现在舜帝身上,并得到了系统化和制度化。说舜帝是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体系的创始人,同样亦不为过。 五、舜帝提高了华夏民族的整体生存能力 民族文明传统要以民族整体生存能力为基础,社会和谐要以全民整体素质为基础,自古至今,概莫能外。世界上的其他远古文明,均遭挫折而中断,唯有我中华文明能延绵至今,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存能力。其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两条:第一是华夏人口数量众多,第二是华夏人口整体质量优良。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来说,人口数量众多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人多力量大,人多种群强,即便重大的灾难和残酷的战争,也是无法灭种的。何九盈先生说:“汉民族长盛不衰,汉语长盛不衰,汉字长盛不衰,人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么多人使用汉语、汉字,文化积累又深又厚,达五六千年之久,即使统治权数次落入少数民族之手,亡国而没有亡种。”[6]何先生的看法非常合理。 那么尧舜禹时代有多少人口呢?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卷十曰:“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二十万八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宋罗泌《路史·发挥六·夏氏户口》从之。皇甫谧的数据,要想得到考古学的证实,几乎不可能。这个人口数据,袁祖亮先生的《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作了初步分析。他认为,根据古籍记载,夏禹时有万国之多,一个“国”大概是一个氏族。根据民族学材料,一个氏族1000人到2000人不等,平均以1300人计算,恰有1300多万人口。所以他认为“西晋皇甫谧所记载的大禹时的人口数据,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能一概否定”[7]。反观袁先生的算法,如果从汉代的户口数据向先秦推,作为大概数据来看,并无荒谬之处。 夏禹时代之所以人口达到1300万,应该归功于尧舜禹实施德政,治理洪水,发展生产的巨大成效。据《尚书·尧典》等古籍,在尧舜时代,早期国家初步形成,华夏实力强盛,大型残酷的战争较少,对外族吸引力大,必然有利于人口生息繁衍。 但是,这时的社会危机仍然很大。一是社会制度的巨变有力地促进了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同时,又加速了部族、民族之间联系和融合,激发了部族、民族间的矛盾和斗争。二是尧帝时期天下大水又大旱,中原深受其害。真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一齐来,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华夏民族的稳定和谐都受到极大的挑战。舜受命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领导华夏民族的胜利渡过第一场巨大生存危机,使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华夏族可能遭受挫折而离散中断了。 当时,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是治水。尧舜命禹治水成功,集中体现了华夏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和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治理黄河水患绝非轻易之事,也绝非只涉及到中原之利益,必须协调各地各族的认识和利益关系,调集各族各地的人力、物力,经过几十年的团结奋斗才有可能成功。我们认为,治水成功的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尧舜时代的社会团结和合作,在于华夏各民族的凝聚力,也在于尧舜禹的全局谋划和艰苦劳动。洪水治理成功,对以农业为生的华夏民族来说,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来说,人口整体质量同样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优胜劣汰,乃是自然的法则。我们认为,民族人口质量主要在于文化素质和精神素质。先进的文化不是自然获得,必定需要精英的创造和推广。华夏民族的文化深厚优秀,离不开舜帝的贡献,这里我们不必再说,只谈华夏民族的优秀精神。 众所周知,华夏民族具有极强的坚忍性和生命力。这种坚忍性是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唯其坚忍,所以能吃苦,能耐劳,能持久,能生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农为本,农耕历史特长,这对中华民族能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农耕民族欲生存下去,比渔猎、游牧、海洋民族更加需要辛勤劳动和耐心的培育;农耕民族更加依恋于土地,除了努力奋斗建设自己家园之外,别无他所。这是华夏民族优秀精神形成的生态环境原因。而弘扬光大这种精神,影响千秋万代的,就不能不赞颂舜帝。 舜从小就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这磨炼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养成了他勤劳节俭的习惯。据《史记》和《尸子》等古籍,舜曾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灰于常羊,就时负夏,贩于顿丘,债于傅虚,籴于平阳,牧于潢阳,历尽了各种劳作的艰辛。舜帝成为天子以后,仍然坚持亲自劳作,不求安逸。《吕氏春秋》说:“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予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管子》亦曰:“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封土为社,置木为闾,民始知礼也。”这些记载都证明舜帝一生勤劳,未尝暂息。 舜帝又力戒逸侈,一生过着十分俭朴的日子。《史记》说:“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韩诗外传》卷三也有同样的记载:“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馀获罪;饭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农不以力获罪;麋衣而蛰领,而女不以巧获罪。”此说基本可信。陶寺遗址已经出现了少数大型高等墓葬,反映当时的贵族或君主确实聚集有较为奢侈的物质财富,而大量的中小型墓葬则反映出低级官吏和群众还是较为贫苦的。那么尧舜保持俭朴作风,当然是有意为之,不愿增加臣下负担,而不是臣下不能提供。故《墨子·节用中》曰:“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韩非子·五蠹》则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橼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霓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持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故传天下而未足多也。”韩非子虽然承认尧舜生活俭朴,但却认为尧舜之时,等级贫富尚未分化,君主与臣下一样又苦又累,故禅让天下其实于自身无损有利,于道德并无高尚可言。显然韩非子是故意低估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也是为了否定尧舜的高尚道德和贬低儒墨的禅让说。既然为君艰辛,尧舜乐于禅让,又何必篡位呢?天子既然和监门同一服养,与臣虏同样劳苦,尧舜禅让君位之后,非臣即民,又怎能“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呢?可见韩非子的说法不通。《韩非子·十过》又有一则独特的记载:“尧禅天子,虞舜受之,作为食器,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入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这似乎又认为尧舜之时,君王已有特权享受,脱离了群众,与上面所说的尧舜节俭艰苦与民众相同的说法相矛盾。这是韩非子对尧舜传说态度暧昧,动摇不定的结果。总之,《韩非子》广储舜帝异说,仅为驳儒家而已,并非真的在意舜帝传说何者较为可信,明显具有战国纵横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习气,我们对韩非子的说法,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因为舜帝一生勤劳节俭,历尽艰辛,所以才能成就一番事业。若非舜帝在家备受折磨,怎能成其孝名,树立起五典伦常?若非舜帝流浪四方,百苦遍尝,众业皆为,怎能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又怎能遍入百官,百官时序?所以孟子感慨良深地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所赞颂的著名代表,第一个就是“舜发于畎亩之中”。可见,在艰难困苦之中,舜帝将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发扬光大,对提高华夏人口精神素质,提高中华民族的意志和生命力,具有永恒的榜样激励作用。 注释: [1]张光直:《早商、夏和商的起源问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2]谢宝笙:《尧舜禅让与五帝文化》,《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 [3]周先民:《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 [4]何光岳:《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5]陈唯声:《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北方论丛》1996年第4期。 [6]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8]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分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页。 (《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 X4 q3 _5 U- j- e+ _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