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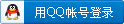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试论尧舜时代与国家 葛志毅 一、孔孟对尧舜的传述 我们对尧舜历史的认识,除经由孔、孟传下的最早文献记载《尚书》之外,还有他们自身对尧舜的相关论述。如对这些资料加以分析,不难发现在他们的观念中,确以尧舜为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开端。如《汉书·艺文志》在论及儒家的学说宗旨时有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以尧舜与周代文、武二王并列,认为他们是中国古代圣君的最初楷模,尧舜身份与三代之王无异。出于这种认识,于是有孔子删《书》断自唐虞之举,取尧舜冠诸三代之前,列为百世帝王之首,供历代取法。《论语·尧曰》述圣圣相传心法时,由尧舜起;《孟子》篇末列历圣相传大数时,亦由尧舜起;此外,《论语·泰伯》篇末亦历数尧舜禹及周武王相承治天下之功德,似此皆与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的宗旨相符。由儒家相承的圣人道统从尧舜起的事实,可见自孔孟起从未把尧舜与其后的历代帝王在身份性质上加以区分,即事实上乃视之为文明国家的最初君主,而非野蛮时代的末代酋长。《论语·泰伯》载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是视尧为法天而治之君,亦即君临下民的天子。至孟子则屡称“尧舜之道”(《孟子》之《公孙丑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万章上》、《告子下》、《尽心下》),试考所言,“尧舜之道”包括孝悌、以仁政平治天下、赋税征收制度等,都是应包括于国家制度内的种种因素。 《尚书》经史官的最初编辑后,又经孔孟传述,如《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序《书传》”,《孟荀传》谓孟子“序《诗》、《书》”。其中孟子更多引《书》讲述尧舜古史,且内容有不见于今传《尚书》者,故汉儒赵岐谓孟子所述尧舜事除据《尧典》外,亦有出自《逸书》者[1],可见孟子熟稔于《尚书》尧舜古史。如《孟子·滕文公上》载尧时洪水泛滥,乃举舜使佐治,舜乃选任益使掌火焚烧山泽,使禹疏决江河,后稷教民种植五谷,契为司徒教化人伦。核诸《尚书》,《尧典》载舜命禹为司空平水土,弃为后稷播百谷,契为司徒布五教,益为虞。按虞为掌山泽之官,与《孟子》舜使益掌火焚烧山泽合。焚烧山泽又与开荒种田有关,故《书·皋陶谟》又谓禹“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即禹与益边治水边垦田,以解决民食问题。总之,《孟子》所述与《尚书》合,无疑孟子关于尧舜的历史知识应得自《尚书》。此外,在孟子关于尧舜古史的评述中,还可概见到他对尧舜时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如《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按“平”犹言治平、太平。此谓尧即位之初,尚未摆脱国家出现前的混乱无序状态。后因尧舜治理得方,于是天下臻于治平,《滕文公下》:“当尧之时……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离娄下》:“禹、稷当平世”,所谓“平”即国家主导下的社会秩序状态。具体讲,所谓“平”当指禹治洪水之后,在舜之世。《史记·五帝本纪》所言可以为证:“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四海之内,咸载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按舜即位,首先举用禹、稷等二十二人任以政事,分治天下。经此二十二人佐舜治天下,尤其是禹平水患而天下平,此即孟子所谓“禹、稷当平世”,《大戴礼记·五帝德》亦谓舜“举贤而天下平”。天下太平,于是有兴作礼乐之举,如《吕氏春秋·大乐》:“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史记·乐书》:“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故“禹乃兴九招之乐”是太平的象征。“致异物,凤皇来翔”更是太平的祥瑞,如《史记·礼书》:“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可为证。所以《五帝本纪》在兴乐致祥之后结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即谓舜继尧为明德太平世之始,所述与孟子合。总之,孟子所述尧舜时代的社会情状,实乃国家文明肇兴的历史。儒家又称虞夏商周为四代,并认为四代的礼乐制度足为后世楷模。如《礼记》之《明堂位》及《学记》,《大戴礼记》之《四代》、《少间》等皆论及四代。《礼记·祭义》称“虞夏商周,天下之盛王也”。四代之说应始自孔子,《论语·卫灵公》载孔子答颜渊以治国之道有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按“韶”即禹所兴“九招之乐”。孔孟儒家既合称虞夏商周为四代,又以四代制度堪为后世法,那么,四代制度应是同质的。即若以夏商周为国家,有虞亦不当例外。所以从四代的概念与孟子以舜为治平之世论之,至少在舜的时代已进入国家文明。 孔孟固无今日有关野蛮与文明区分的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但他们也有自己关于野蛮与文明的界定标准。如《孟子·告子下》记载孟子论及赋税征收额度时有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是可见孟子关于野蛮与文明区分的认识有其相当的理据。孟子所论,实质上已指出中国与貉之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完全由赋税制度支持起来的国家机器。所谓“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饔飧”及“百官有司”乃是国家机器及其上层建筑,这些完全是由赋税制度支持起来的,而且赋税征收额太小不行,像貉那样二十取一是不行的。孟子所论实际已接触到国家与氏族组织间的根本区别问题。恩格斯在论到国家与氏族组织间的第二个区别时,指出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2]。孟子既指出国家机器及与之相当的赋税制度乃中国所有而为貉所无,也就相当于把当时先进的中原国家文明与四裔落后的部族社会区分开来。这应是当时文化条件下所能提供的有关野蛮与文明的最好界定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又把“尧舜之道”视为理想的文明代表模式。总之,以上的论述表明,孔孟心中的尧舜显然是文明国家的最初君主,而非野蛮时代的末期酋长。 这里附带要说一点,即孔孟所传尧舜古史的可信度问题。与春秋战国诸子相比,诸子多以发明思想义理为主,其中唯孔子儒家偏重于传述古史,但学风又以崇尚征实为特征,因而最具历史学派的风范。孔子曾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但其述古、好古的前提是要“文献足征”(《论语·八佾》)。是以孔子删订六经,借传述古史的形式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孔子“好古”而又重“文献足征”的最好证明。所以不能一般套用战国诸子托古改制的旧说去简单评价儒家传述的尧舜古史体系,而且从司马迁推崇有加的态度中,也可说明孔子儒家所传经典记载的信史价值。因为出于对孔子儒家上述学风特征的肯定,司马迁推之为自己的史学前驱。《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即司马氏父子创意作《史记》乃是上承孔子删订六经的传统。那么,司马迁此言岂不可证孔子儒家实为中国古代史学的百代不祧之祖吗?而且司马迁作《史记》时,大量采用孔子儒家所传六经等古史记载,并有所谓“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以一个大史学家的身份如此尊信孔子儒家所传六经等古史记载,那么,孔孟所传尧舜古史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二、尧治历明时 尧生平做过两件大事,即治历明时与选用人才,其中又以治历明时最为重要,因而被详载于《尧典》篇首。据《史记·孔子世家》:“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则首《尧典》终《秦誓》的《尚书》篇次,乃孔子编排的结果。《尧典》篇首详述尧观象授时事,也由孔子所言可得一点参证。《论语》全书载孔子集中盛赞尧者仅见于《泰伯》之一章,其中又首先说道:“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按言尧为君法天,主要应指《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事而言,是为尧平治天下之初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在此之前,尧曾有过一段得天下的经历,即《尧典》谓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此乃对尧的事业由家而国、而天下渐次发展壮大的过程概括。后来儒家总结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模式,显然与此有关。尧“协和万邦”即统一各部落并初步结为国家,其间也应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只是书缺有间,难以详考,此后即着手各种制度建设。首先就是治历明时,即命羲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用以指导民生农时。治历明时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发展农业生产是为解决民食问题。中国古代很早就以解决民食作为君主治民的首要政务,这在一些论政的言论中亦多有反映,如《书·洪范》载“八政以食为首”,《论语·尧曰》亦曰:“所重民:食、丧、祭。”都以“食”置于治民的首位。而民食与农时密切相关,故《尧典》记舜敕告十二牧时首先指出:“食哉唯时”,孔传:“所重在于民食,惟当敬授民时”,已明确指出民食与农时间的密切联系。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有赖于季节气候的好坏,因此为搞好农业生产,首先应做好治历明时方面的工作,这是中国古代历法发达较早的一个直接原因。《尧典》载尧嘉美羲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功以后,又接着说:“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孔传:“言定四时成岁历,以告时授事,则能信治百官,众功皆广。”足可见治历明时之重要,因其关乎国家百事之兴衰;此又可以解释,何以尧在平治天下之初即首先全力做此事。《论语·尧曰》载尧命舜之辞亦谓:“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此“历数”即治历明时。如《书·洪范》八政四曰五纪,五纪之五曰历数,孔传:“历数,节气之度,以为历,敬授民时。”《史记·历书》引《论语》此文,亦以造历事解历数。所以舜在摄位之初,首先“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即致力于观象治历之事[3]。 尧在完成治历明时这件大事之后,便开始留意于人才的选用。选用人才的最大成功是举舜参政,而舜在摄位期间为推进尧的事业,举措得方并取得相当成绩。如《尧典》谓:“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按三代祭礼因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身份等级之异而有别,这里舜乃是以天子身份主持最高规格的祭礼[4]。《尧典》又谓:“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此乃舜以天子身份朝四方诸侯。这些行为对确立尧舜为首的中央政权的地位威望,意义当十分重要。至于其所行巡守、分州、制礼、作刑诸大端,俨然已建立起天子共主主盟诸侯式的早期国家形式。以巡守为例,巡守乃三代天子统治诸侯的基本监管方式。舜东巡守时,“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其他三方巡守皆与东方同。细绎巡守时所行各项举措,其性质实集中于统一各种相关的文化礼俗方面。这对于从文化上弥合刚刚用政治力量统一起来的各部落邦族,其作用之大是无庸赘言的,从而也为三代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发展奠定统一的文化根基。这一点,往往为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此巡守四方诸侯之制在《论语》中可寻得一些佐证,如《尧曰》谓:“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按舜巡守四方诸侯所行诸事,至少应相当于《尧曰》所谓“四方之政”中的“谨权量,审法度”,乃至注释家们多以《尧曰》所言与《尧典》“同律度量衡”相比义[5]。《尧曰》所言,《汉书·律历志》又谓乃“孔子陈后王之法”,那么,舜巡守所制诸端,至少可为三代国家制度立下楷模。 舜摄位期间的另一件大事是所谓“四罪”,《尧典》:“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万章上》所载略同。历来注释家多以四裔说四罪放杀之地,《史记·五帝本纪》则记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载略同。有注释家说为:“变者,谓流四凶于四夷,使变夷狄之俗,同于中国,盖用夏变夷。”[6]甚是。可注意者是其时已出现中国与四夷亦即所谓夷夏之别的现象萌生,故《尧典》载舜有“蛮夷猾夏”之言,不能谓之全然无据。尧舜禹时代三苗曾为大患,如以《尧典》参诸《史记·五帝本纪》,四罪之中兜、共工、鲧或因举人不当,或因试事淫辟无功而受放杀之罚,惟三苗因屡作乱于江淮、荆州而被迁,反映出三苗在各族中武力攻击性之强,故对尧舜治理下的秩序威胁也最大。《尧典》在载舜举用众贤致“庶绩咸熙”之后,又附缀以“分北三苗”一语为特笔;《皋陶谟》载禹述治水有功而“弼成五服”及十二师、五长“各迪有功”后,即以“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告诫舜;《禹贡》于雍州特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说明谪迁后的三苗在西方安定下来。借助这些记载,已可推见到尧舜时代与三苗斗争之剧烈。由此三苗及四罪之例又可推见到,尧舜时代的统一联盟并未消弭各部落邦族间的矛盾,因而在杂错并处的各部落邦族之间,往往因彼此间的利害冲突而导致互相攻伐。尧舜部族之外的一些部落因失败被迁往四边蛮荒之地,因此逐渐演成文化上的中国与四夷之分。《禹贡》已有“中邦”与“四海”之分,中邦者中国,四海在《尔雅·释地》中说为:“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亦即所谓四夷。四夷之地又称为四裔者,本皆中国族类而败谪迁徙者之裔胄散处四边者也。如《国语·周语上》:“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者,于是乎有蛮夷之国”,可证四裔蛮夷本有自中国迁流而出者,《左传》文公十八年谓舜流四凶,“投诸四裔”,与此合。《左传》襄公十四年:“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是流四裔者包括中国王侯之后。《国语·鲁语上》载里革书曰:“夫莒太子杀其君而窃其宝来,不识穷固,又求自迩,为我流之于夷。”可证春秋时犹保存中国流徙罪人于四夷的旧俗。总之,由舜放杀四罪之事,可见尧舜时代已萌生中国与四夷之分,这种区分的标志主要是文化上的,即当时条件下的国家文明与部落社会间显示出的先进、落后之分。继尧舜时代发展起的三代社会仍无明确的疆域领土概念,但其按中国、诸夏、夷狄的内外划分层次设计出的畿服制,却是接续尧舜时代奠定的中国与四夷之分的格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按中国、诸夏、夷狄之序划分出的内外层次,既非如某些人所指斥的乃畿服制的纸上空谈,亦非公羊学三科九旨中空设的文例,而是确曾实行过,这在春秋时代仍可考见其遗制。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所以禁暴于诸侯也。筑五鹿、中牟、盖与、牡立,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权于中国也。”可见春秋时齐桓公为抵御戎狄、保卫王室与诸夏诸侯,确曾按中国、诸夏、夷狄的地域规制修筑防御关隘。秦汉以下,中国与四夷之分的观念,又演为严夷夏之防的传统在历史上继续发挥着较大影响。若寻溯其源,则不得不由尧舜时代谈起。因为从《尧典》“蛮夷猾夏”、“蛮夷率服”诸语,反映出当时已产生夷夏分合形式的政治斗争关系。 三、舜设官分职 尧去世,舜结束代尧摄政之职而即位亲政。舜自即位始,即留意选用人才,同时实施设官分职制度,并确立了考绩黜陟制度,完成了尧舜时代的职官体制建设。 尧时已注意到举用人才的问题,如他征用舜就是最大的成功。但他在这方面仍有未尽善之处,并为当时及后世所指出。如《皋陶谟》载皋陶论为政重在“知人”和“安民”,禹认为尧于此犹有不及,并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忧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即指出尧在举用人才方面的失误与不足。春秋时鲁季文子谓“八元”、“八恺”“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又有“四凶族”“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舜则举八元、八恺任用之,流放四凶逐去之,“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是舜继尧为天子,其举用人才之当是很重要的一点。舜在举用人才的同时,确立和完善了选举考绩制度。如舜在摄政时厘定制度,其中之一是:“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是乃巡守、朝觐诸侯之制,并包括诸侯述职、考绩之制,故曾运乾谓:“敷奏以言,述职也;明试以功,考绩也;车服以庸,酬庸也。”[7]甚是。但其制亦通用于一般的选举考绩之用,故《皋陶谟》载禹陈述选举考绩臣僚时有曰:“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试)以功,车服以庸。”关于考绩的具体时间程序,据《尧典》所载为:“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这种考绩制度在尧时已在行用。如尧咨举人才时有谓“若时登席”,于举舜则曰“我其试哉”,谓共工“静言庸违”,四岳举鲧则曰“试可乃已”,诸所言皆准“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选举考绩制度内容而发。鲧与舜之黜陟也确因考绩结果所致,如《尧典》载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于是有“殛鲧于羽山”之刑;尧举舜陟帝位时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据此则尧时选举考绩制度已在行用,至舜登位则举用二十二人,使各有其职,于是设官分职之制告成。因为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尧时职官设置尚不完备,于是舜先后命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契为司徒,皋陶为士,垂为共工,益为虞,伯夷为秩宗,夔为典乐,龙为纳言,至是职官粗备。由选举考绩制度结合设官分职制度,于是初步形成一套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由于中国古代“天下国”的性质,致使其在国家疆土的规制上,不可能有明确的领土疆域概念,但尧舜时起已大体维系一个具有土地四至和由“万邦”合成的国家政权组织。如《尧典》谓尧“光被四表”,孔传谓“东表之地称嵎夷”,那么,羲和四子所居东南西北之地即可目为尧时的“四表”。《史记·五帝本纪》则载明舜时声教所及四至之地:“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载略同。在此四表、四至之内布列有“万邦”,如《尧典》:“协和万邦”,《皋陶谟》:“万邦作义”,“万邦黎献”。与此万邦相关,是被称为四岳、群牧、群后、有土、有邦等内外诸侯长伯。他们同为尧舜之臣,即《皋陶谟》载禹所谓:“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是尧舜居万邦诸侯长伯之上称“帝”,有天下共主之尊。共主“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的制度形式,使之具有如同三代国家般的性质。如再结合对舜命官分职所建统治体制的分析,可进一步证明此性质。 舜所命诸官前已述及,此处仅就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例深入分析。如舜命伯夷典礼。何谓礼?礼即等级制,乃根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之异,在物质享用方式上做出的等级制规定。《尧典》谓舜巡守“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郑玄说以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之礼[8],虽未必全是,但他知道等级制与礼的本质联系。考《周官·大宗伯》载:“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此殆即伯夷所典三礼,汉儒皆如此解[9]。《大宗伯》此下又详述吉凶宾军嘉五礼、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诸礼仪。其中除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外,其余诸目殆略相当于《尧典》之“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孔传以吉凶宾军嘉说五礼,其五玉相当于六瑞,三帛二生一死贽相当于六禽。《大宗伯》所述乃周礼大纲,应渊源有自,与《尧典》略相合亦不足怪。而且如六瑞、六挚皆明言为“等邦国”、“等诸臣”而设,尤足证明礼的等级制本质。因而就伯夷典礼一事,可见当时至少已是等级分层的社会。又据《大戴礼记·五帝德》曰:“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史记·五帝本纪》:“伯夷主礼,上下咸让”,所谓“节”及“上下”都与等级分层制度有关。《书·吕刑》又载:“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世本》亦谓:“伯夷作五刑。”故汉儒谓伯夷有出礼入刑、制礼止刑的观念[10]。此亦非不可能。因为《吕刑》又谓:“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维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于棐彝。”这显然是主张以刑辅德,以德导民,此又下启周人“明德慎罚”、“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的思想(《书·康诰》及《吕刑》)。像上述以刑辅德的主张,最终要归结于导民于礼的目的。总之推原其故,很可能是刑礼相须的复杂现实,迫使伯夷在主礼的同时又不得不典刑,因而这从另一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分层制度化的现实。因为既由礼的推行可证其时已是等级分层的社会,那么,“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很可能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先声,此犹《荀子·富国》所言:“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质言之,礼以待贵族、刑以待庶人的原则,起自“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的举措之中。那么,由伯夷典礼一事,益可见其时贵族与庶人间的等级区分,而贵族与庶人,或曰君子与小人之分,是此后三代社会的基本阶级差异。又舜在命皋陶为士掌刑时有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即外有蛮夷乱夏之忧,内有寇贼劫杀之患,需要用刑加以防禁。又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据孔传,即行刑之所有三处,大罪刑于原野,大夫刑于朝,士刑于市。是当时的刑乃兵刑不分的形态,兼具内外的职能,即对内用以维系社会治安,对外用以抵御寇犯之敌。那么,据刑所具有的这种内外职能而言,它不是已构成国家手中的合法暴力机构吗? 此外,纳言一职则反映出君主独擅的专制百官之权。舜命龙为纳言之官时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传解为“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的“喉舌之官”,从而使纳言之职的性质受到误解。其实仅从字面上已可看出,舜要纳言传达的乃是对“谗说殄行”的惩罚之命。因此纳言之职的本质在于,它反映出专制百官的独擅君权,而宣命于下与纳言于上的喉舌之职尚在其次。此可由《皋陶谟》所载得到一旁证,如其载舜言有谓:“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这主要讲对“庶顽谗说”之臣的黜罚。即先是以各种手段惩罚之,继之以观其效,改过者则进用之,不能改过者再严惩之[11]。此“庶顽谗说”即《尧典》所谓“谗说殄行”,即不合君意的言行不轨之臣,故为舜所痛恨。《皋陶谟》载舜言又有谓:“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按“在治忽”乃古文,《今文尚书》作“采政忽”,《史记·夏本纪》索隐引刘伯庄说云:“听诸侯能为政及怠忽者”,所解颇是。此句所言乃是根据《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及“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的道理,借助音乐窥知天下民俗,由此又进知政治得失,如《尚书大传》载舜巡行天下而贡八伯之乐,即是其事。故“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即谓借助音乐审知政俗得失,然后据以行赏罚。“出纳五(吾)言”即《尧典》之“出纳朕命”,此处所言与对“庶顽谗说”的罚黜一样,主要指对臣下的赏罚黜陟权。此外,汉人认为纳言一职相当于《周官·春官·内史》和汉代的尚书[12]。从后二者的职守中,仍可见他们操有协助皇帝黜陟大臣的重要权力。试看《周官·内史》,除其参与机要、出纳诏命的职权外,主要涉及对群臣的黜陟爵赏权,其中要以爵、禄、废、置、杀、生、予、夺所谓八柄之法最为突出。汉代尚书的“典天下岁尽集课事”、“绳纠无所不总”[13]及“掌凡选署”[14]诸职,都涉及对百官群臣的考核黜陟权。这些职权明显沿袭自纳言而来,反过来又充分证明君主独擅的专制百官群臣之权在当时的存在。 总之,从对舜所命诸官体制,如上举伯夷典礼、皋陶作士、龙作纳言诸例的分析中,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具有等级乃至阶级的分层差异;同时,出于维护社会内外秩序及安全的需要,已组织起合法的政府暴力机构;最后,凌驾于全社会与政府之上的最高权力,已表现为兼制百官群臣的专制君权;作为这些因素的集合体,毫无疑问当时已出现国家。 结语 在孔孟的传述中,尧舜是中国古代圣君的最初楷模,其时代是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始初阶段。结合对《尚书》等历史文献的分析,尧舜所创各种制度不仅使当时初步确立了国家的性质,而且又多为是后的三代国家所继承和发展。只是尧舜国家尚未十分成熟,仍带有很大过渡性质。如果套用时下在学界较为流行的国家起源理论,称尧舜为酋邦也许更为合适。按《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史记·周本纪》也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据此,很可能在周代曾对前代,主要是尧舜夏商周的政治称号,加以厘定。所以后来称尧舜三代为二帝三王的说法,应是有根据的。由帝而王的称号厘定,很可能反映出周人或者就是春秋战国时,对尧舜与三代在社会政治及文化历史所存差异的某种体认。这种体认在今日看仍是合理的,故二帝三王的历史概念是可以接受的。后来秦统一,两汉承其绪,创建秦汉帝国的规制,此后直至明清没有大的变化。这样,从尧舜起至清代止的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历史,可以用这样的分期概念予以概括性划分: 尧舜——酋邦时代; 夏商周——王政时代; 秦汉至清——帝制时代。 参考文献: [1]焦循:《孟子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7页。 [3][7]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第18、20页。 [4]葛志毅:《周原甲骨与古代祭礼考辨》,《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 [5]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第1360~1362页。 [6][9][10]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第69、81、444页。 [8]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第45页。 [11]屈万里:《尚书集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41~42页。 [12][13]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6、204、205页。 [14]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3596页。 (《管子学刊》2000年第4期) 7 m1 k& A$ \; Q* w. j: h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