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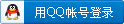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舜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根脉的地位 陈仲庚 一、文化根脉的始原:生命意识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有着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它的复杂性就在于:既可以将人带向理智的巅峰,让人更清醒地认识自我认识人类,从而使人能够特立于生物界并与生物界区别开来,保持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以将人们带向迷茫的深渊,让人在眼花缭乱中迷失自我乃至于丧失人的生命本真。因此,我们应该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找到一个内在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它应该是一切文化现象生发的基点,或者说,是文化大树的根脉所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面对滔滔东逝的流水曾感慨系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这里,孔子所浩叹的“逝者”自然是如箭的时光,但它绝不仅仅是纯客观的物理学的时间,而是与人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更准确一点说,是对人的生命易逝的浩叹。的确,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多少英雄豪杰都被时间之流洗刷得了无痕迹;对普通人来说就更是匆匆过客,似乎是无声息地来又无声息地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因为当人类作为智慧的动物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与世界的区别时,同时也就意识到了自己总免不了一死,既然意识到了生命的存在却又无法阻止生命的自然消失,这其中的悲哀和感慨也就是天然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 当然,孔子的浩叹还不能真正确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真,因为“逝者如斯”不仅仅是指人类,在孔子那里,人的主体意识还不很强。在西方世界,人的主体意识、人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似乎要强烈得多。《圣经》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之所以要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目的是要派他们去管理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圣经还说,人和自然本来相处得很好,而且具有同上帝一样的永恒生命;但由于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劝告,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智慧果,于是受到了上帝的惩罚: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并因此而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力,只能靠一代接一代的短暂生命来维系人类的延续;上帝还让蛇与人世世为仇,让土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使人必须终年劳苦、汗流浃背,才能养活自己。这些说法隐含着一系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其一,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其二,人与自然是敌对的;其三,自然是永恒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其四,人要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这些思想影响深远,在很大程度上铸造了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基本态度,尤其是铸造了西方人强烈的悲剧意识:人生不仅短暂,而且人生来就是遭罪的。 那么,作为智慧动物的人将如何化解自己的悲哀?感慨之后又该如何作为?不同的文化系统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在基督教和佛教那里,都是以背对着人世,希冀在飘渺的天国求得灵魂的永生。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是以自信的微笑面对现实人生,认为人的不朽或永生存在于现实的此岸,而无须到飘渺的彼岸世界去追寻,如道教的办法来得简单而直接,认为只要通过“炼丹服药”或“三关修炼”就可以求得人的长生;儒家则是首先为现实的人生确立其生存的价值,再在人生价值的确立中去寻找其不朽或永生的意义。 当然,从圣经故事中我们还可以窥探到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人类智慧与生命意识的关系。当人类无知无识时,可以与自然界融洽相处,并具有永恒的生命;而一旦有了智慧,便脱离了自然界并丧失了永恒的生命。那么,这种“智慧”的初始内涵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生命意识”。我们知道,当我们说“自然界是永恒的”时,其实是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因为当自然界的一切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时,它们都不是永恒的,都有一个由生到灭的过程;而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忽略”,就因为自然之物没有生命意识,因而不将它们作为个体的生命之物看,即便是生命意识最为宽泛的佛教,提倡所谓的“普度众生”,也仅仅是将动物界纳入生命之物的范畴,没有顾及整个生物界,更未顾及无机物界。因此,如果说上帝所代表的是自然,上帝的永恒就是自然的永恒,那他所代表的也只能是作为整体的自然界的永恒,而并非作为个体的自然物的永恒。那么,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的永生至多也只能是作为人类整体的永生,而决非作为人类个体生命的永生。当亚当和夏娃(当人类尚未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存在时,亚当可以指代一切男人,夏娃可以指代一切女人)的智慧能够判别个体生命的存在时,有关生命短暂和生存苦难的悲剧意识便也接踵而至了。有了这种个体的生命意识,人类就得思考如何把握好这短暂的人生、如何协调好个体的关系以便好好地生存、如何从短暂的人生中求得永生……如此等等的思考再付诸相应的行动,便有了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由此可以说,生命意识是文化根脉的始原。 二、中国文化根脉的始原:尧舜之道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已经成了中国人张口即来的口头禅。中国人总喜欢追索“五千年来古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追索到的终点即为三皇五帝,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始原就在三皇五帝中。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皇五帝其实还可以进一步简化,因为对中国文化真正产生作用的仅有一皇三帝:不可分割的炎黄与不可分割的尧舜(“炎”为“三皇”之一,“黄、尧、舜”为“五帝”之三)。在炎黄与尧舜之中,黄帝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始祖,舜帝被尊为中华文明的先祖,就中国人的血缘崇拜来说,黄帝的始祖地位要高于舜帝,但如果要真正追索文化的起源,尧舜之道才真正具有文化始原的性质,或者也可以说,炎黄是中国人的血缘始祖,尧舜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始祖。中国人往往自称炎黄子孙,而中国的文人则言必称尧舜之道。当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时,也就认同了自己与炎黄二帝的血缘关系,这似乎意味着,炎帝和黄帝是在“血缘”中获得永生的;当我们称颂尧舜之道时,也就认可了其文化价值的存在,那么尧舜就在“文化”中永存。当然,作为生物性存在的血缘,是不能流传永久的,十代之后,先祖的血缘即已丧失殆尽,因而炎黄的血缘其实还是一种文化血缘,或者更确切一点说,炎黄的血缘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完全有赖于尧舜之道的流传。尧舜之道不仅使得炎黄的血缘流传不朽,也使得普通中国人所寻找的永生之途变得简单易行。 那么,尧舜之道的内涵是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中,虽说炎黄联体不可分割,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黄帝;同样,尧舜之道也不可分割,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舜帝。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帝”,其根本点就在于他的“孝感天地”。尧因为重视孝,所以才会选择以孝闻名的舜作为继承人;舜则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既被尧帝所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因此,尧舜之道的核心内涵便在于“孝”,尧舜之道也可简称为“孝道”。 舜帝的“孝感天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从中国古代典籍的一记再记中可以看出。首先对此进行记述的是《尚书》,据《尧典》所载,帝尧要四岳向他推荐帝位的继承人,四岳即以虞舜为荐。虞舜在当时只是个平头百姓,为什么要举荐他呢?四岳提出的理由是:“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不格奸。”即是说,虞舜是在父母及弟弟都对他不友好的前提下,却能与他们和谐相处,像这样孝心醇厚的人,由他来治理国家,应该是不会坏事的。仅因虞舜的“克谐以孝”,尧帝便同意了四岳的意见:“我其试哉!”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下嫁虞舜,以考察其孝行,这其实已经不是“试”,而是在极力抬举,如果仅为一“试”,两个公主作牺牲的代价未免高了点。但尧帝所“试”的结果如何呢?《尚书》接下来仅说虞舜“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即是说虞舜向百姓宣扬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常法,人们都能顺从,而虞舜自己的具体孝行怎样,却没有说。《孟子·万章》则说:“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似乎是将二者结合了起来,使之更具前因后果的逻辑性:“瞽瞍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瞍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擀而下,去,得不死。后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瞍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父母几次要杀他,虞舜死里逃生,但却无丝毫怨恨,对父母仍是孝敬如初,这样的孝行确实可以感天动地,故而到了神话色彩较浓的《山海经》中,说舜耕历山,居然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这样的孝行自然也应该成为国人师范的榜样,所以元代的郭居正在作《二十四孝》时,便将舜帝的“孝感天地”置于篇首。 尤为重要的是,由舜帝的“孝感天地”为基础确立了尧舜之道,并进而确立了中国文化的特色。《论语》曾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孟子》则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即是说,儒家作为思想资源的尧舜之道,经孔孟的阐发成为孝道。中国人不仅是从孝道中确立现实的人生价值,也是从孝道中获得宗教性终极关怀。所以尧舜之道经孔孟之道而形成的孝道,其实是将人生哲学与宗教结合在一起的。 三、“孝道”的价值之一:人的个体生命在“亲亲”中生存 孔子说孝弟为仁之本,那么“仁”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这似乎得从分析“仁”字的原始本义入手。《说文》云:“仁,亲也。从人从二。”段玉裁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又:“按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即是说,“仁”是表示“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相亲”的关系,这就是儒家仁学的出发点。 一般都认为孔子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有人仅从字面上理解,认为孔子的这一思想可以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平等、博爱”思想相媲美。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孔子之“爱人”,不仅有等差,也有范围,并不是“爱一切人”;但这种等差和范围,也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仅限于统治阶级之内。孔子的爱人,首先是圈定在家族成员的伦理关系中,即所谓的“亲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也就是说,人的群居生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但最为重要的关系是“亲亲”。“亲亲”原则当然也不是孔子所首创,它是西周以来宗法关系的核心,这一关系维系了西周数百年的稳定,但到了孔子时代,诸侯们只顾扩张自己的势力,根本不把“至上亲”——周王室放在眼里,而诸侯宗室的内部,犯上作乱的事也屡见不鲜。因此,在孔子看来,“亲亲”不行的主要原因在于犯上的人太多,于是,孔子在“亲亲”原则中便特别强调“孝弟”:“孝弟也者,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将“孝弟”提升到“为仁之本”的高度,足见孔子对它们的重视。那么,孝是什么呢?《说文》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段玉裁引《礼记·祭统》曰:“孝者,蓄也。”段注:“顺于道,不逆于伦,是谓之蓄。”从字形中可以看出,“孝”的原意本是子女服侍父母,父母对其行为作出“好”的评价。如果不孝呢,那罪名可就大了,《孝经·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儒家为什么要将“孝”作为“仁”之本,亦即为“人”之本呢?应该说,“孝”也确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唯有父子关系是与生俱来人人所具有的,是人的一种最原始的关系;而且,在家庭关系中,如果父子关系不稳定,则家庭关系就难以稳定,进而就难以有社会的稳定,所以,就其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而言,也是最为基本的。正因为如此,儒家才将孝道作为仁道之本,而我们要了解儒家的仁道也必须从孝道始。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而儒学的核心是仁学,仁学的核心又是孝道,所以孝道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DNA”。既然孝的作用是在稳定家庭并进而稳定社会,所以孝道其实也就是治国之道。《孟子·梁惠王上》云:“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离娄上》则更进一步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也就是孟子最为理想的所谓仁政。而在《孝经》一书中,“孝”不仅与“治”相关,还分了层次,如《孝治》章说“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圣治》章则谓“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如能用孝“以临其民,是以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正因为明王是以孝治天下的,所以天子之孝也就在于“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邢于四海”;百姓之孝则在于“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教”与“养”的结合,其实也就是“国”与“家”的结合,中国的家与国之所以能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因为有亲亲之孝的原则作为其连接点,即从孝出发归结于治。 四、“孝道”的价值之二:人的生命价值在“尊亲”中实现 百姓之孝重在“养”,这首先是为了保证人的生命个体的物质性生存;但“养”并不是孝的全部内涵,曾子在《大孝篇》中说:“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所以曾子将孝分为三个层次:“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如果说“养”只是人生的基本义务,“尊亲”与“弗辱”则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然而,究竟如何才是“尊亲”,如何才能使父母“弗辱”呢?儒家所提出的办法是守身、修身、友悌、行仁。这四者所强调的是个人与父母及家庭的整一关系,在儒家看来,个人的生死荣辱绝不只是个人的事,而是与父母及整个家庭乃至国家天下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从守身来看,主要是讲对身体的爱惜。《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行孝的必备条件,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行孝便是一句空话,所以《孟子》也说:“守孰为大,守身为大。”而且,守身不仅是行孝的必备条件,也是解除父母之忧的起码孝心,《论语》载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说:“父母唯其疾之忧。”朱熹注云:“言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唯恐其疾病,常以为忧也。人子体此,而以父母之心为心,则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谨矣。”因此,守身的出发点首先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父母。 其次,从修身来看,主要是讲品行的修为。曾子《大孝篇》说:“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故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其身,敢不敬乎?”身体的疾病已是父母之忧,如因行为不端而招致灾祸,当然更是父母之忧,所以修身比守身更重要。孟子则将人生中的不好品行全都归入“不孝”之列:“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些不孝的品行必须通过修身的途径予以根除,才能解父母之忧,并确保父母“弗辱”。 其三,从友悌来看,主要是讲和睦家庭。《论语》载孔子称赞闵子骞的孝行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闵子骞的孝行因何受到孔子的称赞?据刘向的《说苑》所载:“闵子骞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衣甚单。父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谓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无留。’子骞曰:‘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闵子骞宁可自己一人衣单受寒,也不愿带累两位弟弟也衣单受寒,他的孝行即保住了家庭的完整,又和睦了家庭成员的感情,其后母也终于被他的孝行所感动而痛切悔改,由可能出现的“三子寒”而变为“三子温”。因此,孝行不仅仅是对父母,推而广之,还必须做到兄友弟悌,所以在家庭里面“孝”、“悌”两字往往连用。 其四,从行仁来看,主要是讲和睦社会乃至治国平天下。《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果说“友悌”是孝在家庭内的推广,“行仁”则是孝在全社会乃至整个宇宙范围内的推广。从儒家所确定的人生价值的不同层次看,“友悌”只是“齐家”,它所保证的还只是父母的“弗辱”,这还不是最高的孝;而“行仁”则是“治国平天下”,能够治国平天下,这不仅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目标,也是最大的孝、最好的“尊亲”,所以《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儒家的观念本来是反对个人的追名逐利的,但对于“以显父母”的立身扬名则又是极力推崇的,这只是说明了儒家将个人的一切价值都圈定在群体(从家到国到天下)的范围内,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立身扬名,但最终的荣誉则归于群体,所以《孝经》将孝的含义确定为三个层次:“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如果说“事亲”、“事君”所着力强调的是被动地承担义务,有轻视个人独立价值之嫌,“立身”则包含了对个人独立价值的肯定,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奋斗而立身扬名,虽说荣誉要归于群体,但个人也因此在群体的纪念中“不朽”,人生的价值也因此而得以实现了。 五、“孝道”的价值之三:人的灵魂在“血缘链”中永生 孝道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还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它更是中国人的灵魂归宿所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全民性宗教信仰,就因为儒家用孝道解决了灵魂安置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孝道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性准宗教。 中国人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孝敬父母,这绝不仅仅是因为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更为重要的是,父母是一个中介,通过父母与祖宗乃至上天有了联系。《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严父莫大于配天”,孝敬父母与祭祀上帝有了同一的意义,这就使孝道带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只因中国的原始宗教从一开始就规定了严格的等级,直接祭祀上帝是天子的特权,平民百姓只能通过祭祖才能与上帝沟通,《礼记·祭义》云:“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夫妇斋戒沐浴,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与神明交,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这种虔诚的心态及礼节,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才有。尤为重要的是,孝道为中国人解决了生命的来源、生命的归宿和生命的延续问题,而这三大问题是一切宗教所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 首先,从生命来源说,中国人认为生命是一个“血缘链”:“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礼记·郊特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在天—祖—父—人(作为个体的人)这一链条关系中,“祖”不仅可以“配天”,还可以“代天”,“人”通过祭祖不仅可与上帝相沟通,而且祭祖本身也就是祭天,祖与天是可以二而一、一而二地转换的,所以《礼记·大昏解》说:“是故仁人之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此谓孝子成身。”“祖”与“天”之所以能够等同,就因为他们都是生命之源的创造者。在早期人类的观念中,凡本原性造物主都是神圣的,都得尊之为神明,在一神教的宗教中,认为只有上帝才是本原性造物主,所以只允许敬上帝而不允许敬其他神灵;中国人虽然认为“万物本于天”,而在万物的分类之上又有各自的本原性造物主,所以中国就有了众多的神灵,而“祖”因为是人之本原所在,所以人更应该崇敬有加。 其次,从生命的归宿说,中国人的观念是认祖归宗。中国人无不信“鬼”,“鬼”是什么呢?《说文》云:“人所归为鬼。”《释言》亦谓:“鬼之为言归也。”《礼记·祭义》也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人死为鬼,归土为安,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观念。这一观念说明,中国人所希求的不是脱离肉体的灵魂升天,而是肉体与灵魂一同归土。既然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连毁伤都不敢,当然就更不能将它随意抛弃。所以,归土为安的观念仍然是孝道的体现。尤为重要的是,“归土”之“归”是指回归故土,决不能随意地“入土”为安。中国人总说热土难离故土难迁,即使是出门在外的游子也总要叶落归根;若客死他乡,其后人也必须想方设法将灵柩运回家乡归葬。中国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死后之“归”,就因为“故土”是生命的本源所在,是列祖列宗的寿终正寝之处,“归土”并不是回到冷冰冰的泥土,而是回到列祖列宗的怀抱,回到生命的本源所在。能回到列祖列宗的怀抱,这其中的温馨,当然就可以使人心安了。相反,如果抛尸野外成为孤魂野鬼,就成了中国人的最大不幸,与此相联系,逐出家门就成了对不孝子孙的最大惩罚,因为这意味着他将死无葬身之地,势必成为孤魂野鬼。因此,孝道不仅确定了生命的本源所在,也确定了生命的归宿所在。 其三,从生命的延续来看,中国人的观念是传宗接代香火延续。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生命的起源是点与面的关系,上帝是一个点,一切生命都是直接由上帝所创造,中间没有链条性环节,所以生命的存在只是单个的存在,要想获得永生也只能依赖上帝的救助。中国人将生命的存在看做一个无穷尽的链条,单个的人其生命虽短暂,却是链条中的一环,借助这个无穷尽的链条,就可以获得永生;而且,就如同归土为安不能抛弃肉体一样,中国人的永生也必须是肉体和灵魂的共同永生。肉体的永生是借助传宗接代来实现的,朱熹曾说:“然吾之身,即祖考之遗体。祖考之所以具为祖考者,盖具于我而未尝亡也。”祖考因我的存在而“未尝亡”,那么我就也可以因子孙的存在而“未尝亡”。灵魂的永生则是借助祭祀的香火来实现的,孔子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祖当然祖就在,当我成为“祖”时,儿孙们祭我,我也就“如神在”。另外,灵魂的永生还可以借助“志”来实现,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子承父“志”,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当然义务,所以愚公移山才那样充满自信,他不仅相信子子孙孙是不可穷尽的,而且相信子孙们会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挖山不止,在这挖山不止的过程中,愚公之“志”也就可以永生了。正因为传宗接代香火延续既关涉到自己的生命,更关涉到祖宗的生命是否得以永生,所以中国人才把“断子绝孙”看做人生大忌,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最为严厉的孝道规范。 六、文化根脉所系:关注人的生命存在 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特在的现象,有着纷繁复杂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表现形式往往将人们带向迷蒙的深渊,让人在眼花缭乱中迷失自我乃至于丧失人的生命本真。因此,我们应该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找到一个内在的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它应该是一切文化现象生发的基点,或者说,是文化大树的根脉所系。文化根脉所系的东西必定关涉到人的生存,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生存。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能真正起到这种作用的东西便是舜文化。舜文化作为一种简单而概括的哲学性表述,往往被称之为“唐虞之道”或“尧舜之道”,而实质的内涵便是“孝道”,它决定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既维系着中国人的物质生存秩序,也维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需。如果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人的“血缘”之根,它侧重的是中国人的生物性来源,舜文化则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关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如果说某一文化能从人的物质生存、价值生存(或社会生存)和灵魂生存(或精神生存)三个层次上妥善安置好人的生命,那么这一文化就必然具有文化根脉的地位,舜文化恰好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选自《舜文化论文集》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0 j& a$ O1 C& Y) u5 D* I(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