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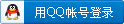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唐虞之道如何可能 张 盈 在荆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不见于传世文献,用语类似《孟子》、旨在阐述尊贤禅让的《唐虞之道》,众学者已从成书年代、文字编连、禅让传说、学术意义等方面加以考察并有诸多成果,至此,在学派归属(属儒家学派)、学术意义(证明上古禅让制度确实存在、暗讽燕哙让位之乱)及从义理对命题的揣摩(篇名定为《唐虞之道》)等问题上达成了大致共识。 本文参考李零先生和黄人二先生的校读本,从义理上试对《唐虞之道》作进一步的追问,以考察对“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解答。 儒家一向宣扬德治与仁政,在最高统治权的传承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又持什么态度呢?目前被认为是现今所见儒家文献中集中论述“禅让”说最早、也是仅有的《唐虞之道》解答了这个问题。“禅让”是上古时君主权位以推选的形式在社会共同体的异姓异氏之间的和平交接。相对于以血亲关系为基础任人唯亲的世袭传承制,禅让制反映了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因此对传授者和承接者的统治观乃至人生态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其他先秦典籍记载的“禅让”说不同,《唐虞之道》没有着重传述如《尚书·尧典》对荐选贤才并试用考察的具体史事,而是通篇围绕“禅而不传”、“爱亲尊贤”的主题展开论述,系统地阐发了“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具体内容和理论根据。 根据李零先生的编排整理,《唐虞之道》开篇第1简至第3简是“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不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愠,约而弗利,躬身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1]。这是文章的总纲,不仅在结构上提挈了全文内容,而且在论证上奠定了整体思路。简文对尧舜“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王道评价很高,认为“禅而不传”是以天下为公毫不自利的表现,并且把“禅”和“利天下”归结到了“仁”、“圣”的德性层面,这就使唐虞之道不仅仅停留在最高统治权交接的政治伦理层面,还深入到了尧舜个体生命的人生修为上,说明王道的兴起是主体的德性修养涵育的结果:“身穷不愠,约而弗利,躬身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身处穷乏而不愠怒,遭遇窘困而不自利,唯有自行修仁而已。唯其如此,才能正身然后正世,成备圣道。 在这里,简文从两个方面回答了“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问题:(1)从“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德行到“仁”、“圣”的德性,是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将王道落实到了人人都能实践的德性修养上,从而使人人都有可能通过修养德性正身正世成为禅让链条上的一环。(2)正身与正世的关系从生命本质的层面为唐虞之道提供了最根本的可能性。所谓正身,即用德性涵化自身,安身立命,己欲立之“立”;所谓正世,即以身作则,己欲达之“达”,正身乃正世之本,正世乃正身之用,正身正世就是内圣外王、忠恕之道,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身以正世,上德以授贤,这是合乎尧舜仁圣之道的必然要求。总之,简文开篇就使“人伦实践——德性修养——生命本质”的解答思路初露端倪。接下来的第4简至第10简及第12、第13简正是从该思路的前两个层面人伦实践和德性修为的培养,论述了可能性的问题。“尧舜之行”把“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落实到了“爱亲尊贤”的人伦实践及德性培养上。 第4简为:“夫圣人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亲也;时事山川,教民有敬也;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大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先圣与后圣,考后而甄先,教民大顺之道也。”正因为圣人是正身与正世的统一体,所以能担当起教民有德的重任,而且先圣后圣不断承启,在各种场合情况下教民以大顺之道。笔者认为这段文字有两处作用:(1)说明圣人的根本任务是教民有德,这是禅让之道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禅让传统合理性的体现,因为只有禅让才能使圣人先后相继,也才能保证对人民教化的满足。(2)利用当时人们对尧舜王道具有普遍的崇尚心理,使人们认识到无论从恢复外在传统的角度还是从自身德性的培养方面,禅让都是合理的。道德的培养和教化也是必要的,从而对当时背离禅让,崇尚暴力的世道进行讽喻,也使现实中的道德培养有了历史上和思想上的依据。 第6简明确提出“尧舜之行,爱亲尊贤”。唐虞之道落实到德行实践层面,就是爱亲与尊贤的关系问题。 “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放,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无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皆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2] “爱亲”源于血缘关系,尤指子对父的爱,在《六德》中,“仁”是子对应的德目,所以说孝是仁的冠冕。“尊贤”指对贤德本身及具有贤德之人的尊敬。将“爱亲”与“尊贤”分别在最高统治权的继承问题上推至极端,就会出现“传”与“禅”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就成了解答“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关键。于是,“唐虞之道”的可能性问题实质上就是“爱亲、尊贤如何统一”的问题。上述简文已从两个层次上给予了答案。 (一)人伦实践层面:文中的“爱亲故孝,尊贤故禅”,为什么不说“爱亲故传,尊贤故禅”呢?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对此有意或无意的评价取舍,因为“传”是血亲关系的自私自利,与“利天下而弗利”的王道根本原则相悖,而“禅”则突破了血亲的限制,唯贤是举,实现了公利原则。可以看出,在统治权交接中,“爱亲”次于“尊贤”,“尊贤”优于“爱亲”,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两者相统一的基础上。 “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就是人伦实践的解决途径。肯定“爱亲”之情的心理根源和伦理情结,推己及人,既立足于亲爱,又超越亲爱,打破血缘纽带的局限,把爱之情平等地遍及他人,成就了人性中本来涵有的仁之德,实现了“仁者爱人”,扩展到了生命伦理的范围。“孝之放”使从血亲旁系外挑选贤能成为可能,所以简文在其后就把“孝”和“禅”提升到了道德的理想层面“仁”和“义”。 (二)德性层面上:“禅之传,世无隐德”,把禅让之制推行于天下,可以使美德张扬,野无遗贤。禅让制之所以能使德性彰显,与它的根本要求分不开。第20简指出,“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3]。禅让,是上位有德之人授予贤者君位的称谓。上位者有德,则天下生民有君而世道清明,授予贤者君位则人民兴于教而为道所化。从中可以看出,在最高统治权的禅让交接中,“德”的因素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德”包涵了“德”和“能”两种含义,并非指单纯的道德。在德与贤的关系上以德为本,“贤”中已有“德”的要求,因此“上德授贤”的贤人,既有贤德又有贤能,并且以贤德为本,贤德的内容包含由德性统摄的“禅而不传”、“利天下而弗利”的王道,这样一来,就使传授君位的人与承接君位的人无论是在内圣还是外王上都具有了同一性,也使禅让制有可能成立、实现及流传下来。 既然在“禅而不传”的“上德授贤”、贤贤相授的交接链条中已强调了每一环的接受者双方的德行及德性,就可以通过“德行”把“爱亲”原则与“尊贤”原则统一起来,而不是失之偏颇,“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从德行的角度看,爱亲与尊贤仍是有分隔的,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只有在生命态度以及爱与尊的德性精神上才能实现,乃至完全相同。“德”正是打破爱亲与尊贤的隔阂,使之统一起来的根本东西,德性的沟通与相融是爱亲与尊贤相统一成为可能的基础。 尊贤首先是尊重德性,把爱亲原则及其所包涵的德性精神融入其中。血亲系统所包涵的德性精神是“爱”,对自身有爱,对他人尤其是血亲的父母也有爱。把这种爱推扩出去,既化解了血亲系统的偏私,又张扬了德性自身的伟大。把亲爱推扩到仁爱,“仁者爱人”,尊贤就是“爱人”的结果。 总之,唐虞之道是以“德”为本、以德相传、上德授贤的贤人政治,“仁”、“圣”二德和“利天下而弗利”是其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条件。 简文随即用“尧与舜”的实例来说明“唐虞之道”在实用上是如何可能的。之所以举舜为例,一是因为舜在三代禅让的传说中处于尧、禹之间,具有承接者和传授者的双重身份,可以独立地构成禅让制链条中的一环,从他身上可以很好地体现主体的德性涵育对禅让制继承性的作用;二是他“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本身的经历就是爱亲与尊贤、贤德与贤能的统一。第一,第22至25简:“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象□□,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尧之所以选中舜,是因为见舜有爱亲的德行如“孝弟慈忠”等,以此判定他具有贤德,能胜任君位。这也是德性在伦理与政治、内圣与外王之间有贯通性的体现。第二,舜能尊贤,与上述构成爱亲与尊贤的统一。第9至10简、第12至13简,都是舜钦命诸臣分治天下的记载,结合《尚书·尧典》可以看出,舜能唯贤是举,知人善任,因材施政,真正做到了尊贤,使各贤人能各尽其才。第三,舜自身体现了贤德与贤能的统一。舜的贤能受到了各种苦难和艰辛的考验,贤德也是无庸置疑的,于是能在贤贤相授的禅让制中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具备了仁圣之德的基本条件,并且探讨了人伦实践和德性层面的可能性后,简文又探讨了面对时命如何可能的问题。第14至15简指出:“古者尧生为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未尝遇[贤。虽]秉于大时,神明将从,天地佑之,纵仁圣可举,时弗可及矣。”尧之所以有天下,是因为生为天子,而且具仁圣之德,逢遇时命,但这还没有完全突破血亲世袭制。只有在天地、神明、人我、时命的四种维度上,由德性流贯其中,才有可能承继君位。 如果即使仁圣之德完全满足了禅让制的基本要求,而时命不到,那么人们又该如何呢?这里似乎与如何实现唐虞之道已没有联系,但这恰恰是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最根源可能性,也是开篇提出的正身与正世关系的内涵。第11简“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政,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知[天下]之政者,能以天下禅矣”,将禅让之理从“养性命之政”的正身本原上探源,说明禅让的可能性根源于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彻底参悟,包括对物质生命必然性的认识,对精神生命的德性本质的通达。第15至第19简“夫古者舜处于草茅之中而不忧,登为天子而不骄。处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不专也。求乎大人之兴,美也。”舜处逆境而能乐天知命,善养性命之政,也才有“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的豁达。这表明舜已完全参透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才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天命所在,分定故矣,对外在物欲、权欲的渴求也随之消散,“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只有如此,才能纯化贤贤相授的王道。“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这段话主要说明圣人基于对物质生命的认识,顺应天命,在肉体和德行方面均不能担当君位时主动让贤,也是“利天下而弗利”的王道的体现。为什么会客观地认识到肉体生命的局限性,又能顺应天命,自觉地致政他人呢?时命的限制只是外因,而内因仍然在主体的德性修养上。 “今之一于德者,未年不一,君民而不骄,卒王天下而不疑。”乐天知命、养性命之政、养生弗伤,最根本的还是以“德”知之乐之养之安之,只要“一于德,未年不一”,就会顺从德性的流变贯通,广施功夫,消解时命的限制。“德”的根本精神是“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实践上则力求达到“求乎大人之兴”。大人即指圣人,同样具有崇高伟大的德性生命。 总之,通过德性的流通实践,消解了时命对“唐虞之道如何可能”的限制,使“利天下而弗利”的王道能一于德,至仁至圣,爱亲与尊贤相统一,禅而不传,则能正身,然后正世。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唐虞之道最基本的可能性,而德性修为和人伦实践则从动态上实现了这种可能性,“人伦实践——德性修养——生命本质”的解答层次昭然已揭。 比较《唐虞之道》与其他记载禅让的文献,《唐虞之道》中的观点在这些文献中或有佐证,或为补充,或相抵牾,所以无论是成书年代还是学派归属问题都很复杂。其他学者已有专门研究,不再赘述。在此只举《孟子·万章上》作一比较。 孟子强调“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孟子借用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唐虞时实行的禅让制,与夏殷周三代的父传子继承制的实质是一样的,这个实质就是都符合天意,顺乎民心。孟子从天命和德性的高度上维护了儒家基于天理公义的禅让制,但又有所变通,认为在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这种变通还反映在回答万章的尧舜相继问题上,孟子认为“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认为天子可以推荐异姓氏的接班人给“天”,但不能强迫天、代替天决定把天下给他,授予天下的主动权仍在“天”处,因此还是不能算天子授天下。这实际上还是“君权神授”的思想。“天”又“不言”(与孔子的“天何以言”思想相符),只是借老百姓对君位接班人的行为和工作来间接表达,“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是所谓“天与之,民与之”。 针对禹后德衰传于子的问题,孟子也给予了一致的解释:益不能由接班人的身份顺利继位,是因为启很贤明,能认真地继承禹的传统,长久地施泽于民。民心所向,天意所为,即使禹向天推荐了益,但启的贤明最终赢得了百姓和上天的青睐。 孟子也没有否认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也没有否认“选贤举能”的传统,只是将向上推荐的最终层次和决定权留给“天”,把“唐虞禅”还是说成“天与之”,天所废弃的是桀纣那样的昏君暴主,而不是启这样的贤君。 以上可以看出,“其义一也”的含义就是天命和贤德。这与《唐虞之道》的义理是相互贯通的。但孟子考虑的是权力交替的同一性问题,在不同的交替形式背后找到“天”这个共同的终极原因,“非人之所能为也”;而《唐虞之道》则将王道落实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上,个人只要注意德性的修养及道德的实践功夫,便可以内圣外王,甚至消解时命的限制,使人的个体生命获得了最大的可能性。 注释: [1]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期,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497页。“身穷不愠”后数句的释文,采黄人二先生之说。 [2]同上,第497页。 [3]同上,第498页。释文采黄人二先生之说。 (《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3期) % f$ h3 e- y& _8 a) h+ {1 r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