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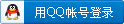
x
舜与中国文化 王富仁 在我看到的学术著作中,把舜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并考察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还是第一部。这给我很大的启发。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观点在该书中已经有详尽的表述,在这里,我着重谈的是我自己读过该书后的一些感想。 一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中国古代哲学、英文学和英文修辞学。据后来成了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先生的回忆,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但他听了几堂课之后,遂感到“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1]。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胡适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这一革新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这对于当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扫除障碍、开辟道路的作用。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了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2]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胡适这个学术革新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必须看到,它给我们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带来了另外一些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带有更根本的性质。 首先,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和中国的文化史?中国的思想史和中国的文化史是不是就等同于中国的书面文化所体现的思想和文化的历史?我们现在经常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就等同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文化,或者更宽泛一点,就等同于由先秦思想家所开创的中国书面文化传统,与胡适的这种文化观念是有莫大关系的。显而易见,这样的文化观念,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人为地简化成了一条或者几条文化的线索,并且就把这样一条或者几条线索当成了全部的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把这些书本中的文字话语就当成了中国人思想和道德的总和。 第二,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是不是考证就是研究中国历史唯一的基础方法?这在从先秦到当前的历史研究中看来是这样的。但假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文明史不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而是在那以前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那个漫长而又漫长的历史时代里,是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的,仅仅用考证的方法根本无法确定被后来人叙述出来的那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当代的考古发掘可以了解那时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但却无法证实当时人们的感受和认识。那么,它们还有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假若还有,这种“历史的真实性”又应该怎样理解、怎样予以确定?也就是说,除了考证之外还有没有另外一些基本的方法以保证对这样一种历史做出有效的研究呢?实际上,即使对于有了文字记载之后的中国历史,仅仅用考证的方法也是无法进行更有效的研究的。对于一个历史家,一个时代的文字记载与其说是考证新的历史事实的依据,不如说更是历史家研究的对象。历史家的任务主要不是了解历史是怎样被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文字进行表述的,而是了解在知识分子文字表述背后的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怎样演化和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仅仅用当时的文字记载能够考证清楚吗?不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我们的历史家运用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了解从当时的大量文字记载中感受出来、发展出来、整理出来的。考证出来的历史不是那时真实的历史。 第三,我们经常说中国文化的“根”,假若我们就把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文化当做中国文化的全部或主体,我们中国文化的“根”也就只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学说中去找,并且在通常的情况下是把孔子的儒家文化学说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但在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中国文化的“根”,而是中国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的枝和叶,中国文化的“根”存在于这个历史阶段之前的中国历史中,并且那个历史阶段与这个历史阶段的特征是根本不相同的。这样,我们的文化研究中也就出现了以枝叶代根干的情况。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把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主要理解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士”这个阶层形成之后的历史,并且把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就主要理解为这个阶层的思想和文化,才导致我们每一次的文化寻根都首先回归到先秦儒家文化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学说中,并且每一次的文化寻根行动带来的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精神联系的加强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增长,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更大分裂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削弱。 只要从这三个方面考虑,我认为,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把舜文化从整个中国文化中提取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进行研究,进行思考,就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了。 我们不能说它寻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根”,但至少,它更加接近了中国文化的根部。 二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把中国文化的“根”直接归结到先秦儒家文化学说的文化寻根行动引起的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精神联系的加强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增长,反而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更严重的分裂和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削弱呢?在过去,我们往往将此归结到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上。但只要我们进入到中国文化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之中去,就会很容易地发现,它的更根本的原因还不在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先秦儒家思想学说本身就不是在中国文化的趋同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分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即使在先秦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中,儒家的思想学说也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只是其中的一家一派。它在后来虽然受到政治统治者的有意提倡,但却始终没有统一起全部的中国文化,它充其量只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个主要枝干。不言而喻,将这个主要的枝干绝对化,就等于将其他所有不同的文化学说逐出中华民族文化之外,抹煞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自然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分裂和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削弱。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呈现的是分化发展的趋势,但这个发展却是在一个统一的根茎上进行的。这个统一的根茎就是更早时期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而作为它的根本标志物的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尧、舜、禹。 对于尧、舜、禹这三个政治帝王存在的真实性,我们是无法通过科学考证的方法予以证实的。后来人关于他们的任何叙述,都可能带有传说的、想象的成分,都可能是“不真实”的,但在所有这些“不真实”的传说和想象的背后,却有着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有着我们先民对世界、对人类、对政治及其领袖人物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正因为后来人关于尧、舜、禹的任何具体叙述都有可能是不那么真实的,所以我们更有必要首先抛开那些具体的事实而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想象那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我认为,只要我们撇开各种现成的历史分期的方法,仅仅用我们最朴素的感知方式感知那时的社会和人,我们就会知道,他们实际出现在中华民族从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的过程中。这个转换可能在更早一些的时间里已经开始,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历史回溯中,尧、舜、禹则是这个转换过程中最早而又最具历史确定性的几个政治帝王。我们所说的自然社会,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状态:在那时,中国社会已经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但这个形成过程是自然的,而不是当时任何人的一种自觉追求。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分散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部落群体,通过部落或个人的迁徙和流动,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正在加强,但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形式,把这些分散的部落联系成一个跨地区的社会整体。所谓“有巢氏”,所谓“燧人氏”,所谓“神农氏”,实际上都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帝王,他们即使有一个原型,有一个具体的所指,也只是在中国社会上有着比较广泛影响、在生活和生产的技术上有过特殊才能的个人或小的部落的首领。这样一个国家的形式,首先出现在黄帝时期。在那时,由于少数部落的强大以及对多数部落的威胁,更多的部落开始联合在黄帝的周围,通过争战,开拓了疆土,出现了一个凌驾在所有这些部落之上的国家机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显而易见,这时的国家形式还是非常简单的,黄帝也主要是一个“习用干戈”、能征善战的军事首领,还没有与他统治下的人民建立起互动的关系。到了尧、舜、禹的时代,国家的作用才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尧、舜、禹这三个著名的政治帝王。显而易见,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上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掺杂着人们的猜测和想象流传在当时的社会上,同时也以口头的形式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国家的形成,整个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自然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群体,凌驾在所有这些个体和群体之上的就是自然,就是天和地。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和地好像和人一样也是有意志、有喜怒哀乐等人的情感的,但自然是一个神秘的整体,人对它的意志就只有猜测而没有决断,这表现在人与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上,由于各自是以自己的形式猜测自然的意志的,因而它无法起到压制一方而支持另一方的实际作用,整个社会关系仍然呈现着无政府主义的无序状态,没有统一的法律,也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国家的出现,整个地改变了社会的关系,也逐步地影响到人与人关系的改变。在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凌驾在每一个人、每一个社会群体之上的国家政治统治集团。这个集团不属于任何一个其他的群体或个人,但又与任何一个其他的群体或个人发生着直接的关系。围绕着它的产生,社会被自然地分成三个部分:国家、人民、盗匪。盗匪或者是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或者威胁到国家政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或者是兼而有之,但不论怎样,它在国家中是少数的人,被国家宣布为坏人,是国家权力必须消灭的对象。国家政权也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它必须依靠国家多数人的服从或支持,人民就是国家必须依靠的多数人,国家的经费支出必须由人民负担;兵士必须从人民中征调。国家政权的生命就是权力,而其权力的基础则是在人民的服从或支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国家政权的内部,则由君和臣的关系构成,君起的是核心作用和领导作用,但他是“孤家寡人”,他只有依靠众多臣僚的服从和支持才能实际地统治整个国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除此之外,在自然社会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然保留下来,这在“君”这里,表现为“君”与“天”的关系。不难看出,尽管当时的国家还是一个雏形,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其主要结构形式,它已经是完整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其具体称谓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名目,其内部结构也日趋复杂,但在国家政权内部存在的还是一个君臣关系,在整个国家中存在的还是一个国家、人民、匪盗的关系,在外部存在的还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必须看到,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首先通过当时政治帝王意识的变化而发生的。仅仅军事的征伐无法导致国家的出现,它还必须建立在政治帝王长期维持对占领地统治的愿望之上。在这时,政治帝王意识到的是自己对这个政权、对这个国家的责任。他已经不能仅仅顺从个人刹那的欲望、一时的意愿而生活,还必须考虑到如何继续维持这个政权的存在。为此,他就要顺从“天”的意志,让国家政权的敌人感到畏惧,让他统治下的民众感到安全和幸福,让他的臣僚听从他的指挥、忠心为他的政权服务。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政治帝王无法回避的问题,国家的观念、政治的观念、权力的观念、帝王的观念、臣僚的观念、人民的观念、组织的观念、部分与整体的观念、分工与合作的观念、法律的观念、道德的观念、经济的观念以及与这些观念相应的天道观念、人道观念、等级观念、礼仪观念、策略与方法的观念等等,都在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这是一整套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是适应着国家产生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而产生的,它改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和人生观念,也改变着中国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但是,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还不具有明确的思想形式,都还自然地包孕在政治帝王自身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包孕在他们的人格模式中。也就是说,政治帝王这个人本身就是所有这些思想的载体,人们从他的存在中就可以感受或认识到全部的国家学说。假若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也有一个关键词的话,那么,“圣人”就是那时的一个关键词。那时的“圣人”观念与后来中国的“圣人”观念是有根本不同的。后来中国人的“圣人”主要指的是像孔子这样的知识分子,而在先秦知识分子里,“圣人”则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贤明的政治家,它与“圣人”这个词是混用的,而尧、舜、禹则是他们共同认可的三个“圣王”。 三 权力是整个国家大厦的支柱,没有权力就没有国家,但权力又是导致整个国家大厦倾覆的主要力量。严格说来,维系国家命脉的权力并不是所有形式的权力,而是国家集体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而产生、而存在的,而不是为维护任何一个个人(包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而产生、而存在的。但是,在任何国家形式中,国家权力又都必须交由个人来掌握、来使用,否则,这种权力就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权力,无法有效地实行国家的管理。这就为国家权力的私人化提供了可能。私人化的权力是游离在国家集体权力之外的另外一种权力,不论这种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都是削弱和瓦解国家集体权力的一种破坏性力量。它导致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从内部削弱乃至瓦解国家这个政治实体。 一般说来,在从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的过程中,政治帝王的个人权力也就是国家的集体权力,而国家的集体权力也就是政治帝王的个人权力。在自然的社会中,人们是没有国家意识和社会整体意识的,国家意识、社会整体意识首先产生在当时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中,他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将原来分散的权力集中在整个国家亦即自己的手里,这就需要特定的才能,特定的个人情操,需要一种为国家整体的利益而忍辱负重的精神品质。一个飞扬跋扈的人是不可能将原本分散的各部落群体联系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集体的。对于一个人,它不但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而且是一个过于沉重的事业。这就使普通民众和下级官吏对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更强烈的觊觎之心,国内的权力斗争主要集中在国家与那些不愿归顺国家的少数部落之间,在这种对抗中,胜利者当然是拥有国家权力、得到多数部落群体拥护和支持的政治帝王。而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之下,当时的政治帝王就更有余暇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事业,从事于能够加强民众与国家相互沟通、相互了解的人文教化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有效地强化着政治帝王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反对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使人“畏”;拥护者会受到政治帝王的保护,获得安全的保证以及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令人“敬”。在自然社会中,也有受到人们普遍敬仰的人物,但那些人物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敢或个人的聪明才智。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但当国家出现之后,这些个人的英雄就被国家权力的利刃切割成了三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成为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盗匪”,不但受不到社会的崇拜,而且会遭到国家权力的残酷镇压,遂以恶名播扬于世;另外一部分则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他们是以对国家事业的贡献和对政治帝王的忠诚而得到国家的承认的,其权威性自然无法上升到政治帝王之上,而那些既非官也非匪的英雄豪杰、才智之士,其影响总是局部的,没有施展他们才能的更加广阔的空间,也不可能得到政治帝王那样的普遍崇拜。这样,在国家权力所自然具有的潜在力量在政治帝王的主观努力下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之后,政治帝王的权威性就渐渐替代了自然社会的个人英雄。成为人们普遍敬畏的对象。在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国家政治统治才开始面临着真正的危险。这种权威性,赋予政治帝王的权位本身一种无比巨大的力量,即使他不再通过实际的努力而争取社会民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社会民众也自然地会敬畏他的权力,服从他的意志,维护他的利益。这样,政治帝王这个职业就变得异常轻松了。他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才能,不再需要忍辱负重的精神,这个职位本身又可以使他成为全国最富有、最有权势、最受国人崇拜并且也是享有最大自由的人。这样的职位,就不能不引起更多人的觊觎了,所有的人在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个政治帝王的生活,即使无法成为实际的帝王,也要利用国家的权力扩大自己的利益、保证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全和幸福。在开始,政治帝王不但是在组织上,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联系整个国家的纽带,而现在,政治帝王则成了所有矛盾的焦点。政治帝王的精力和才能不能不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位上,他的臣僚也不能不以各种形式卷入这样的政治权力斗争,国家的事务再也无法按照事务本身所需要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进行权力角逐的战场。个人权力的斗争是残酷的,以国家权力的名义进行的个人权力斗争就更加残酷,并且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国家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是给人类带来福祉的社会组织形式,但在这种情况下,则成了毁灭人类、毁灭人类幸福的罪恶的渊薮。我们必须看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不仅产生在像尧、舜、禹这样贤明君主的成功的政治实践中,同时也产生在像桀、纣这样暴虐君主的失败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他们强烈地感到了国家政治的严重危机,感到了现实政治的混乱和黑暗,他们才把目光转向了尧、舜、禹这样一些古代的政治帝王,并在有关他们的传说中发现了他们现在仍然感到十分重要的东西。假若说“圣王”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学说中的第一个关键词,“暴君”就是它的第二个关键词,它是作为“圣王”的反义词而出现的。 在考察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时,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更加突出了舜的重要性,这自然与他们家在舜帝陵所在地的湖南永州有关,但在学理上,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即使在尧、舜、禹这三个早期的政治帝王之中,舜的事迹,舜的形象,也更全面、更集中、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由自然社会向政治社会转换过程中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征。 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从国家整体需要对自然、对社会、对人做出的感受、了解、认识和价值判断。它是集体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是节欲主义的,而不是纵欲主义的;是道德主义的,而不是自由主义的。随着中国国家的产生,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也就随之产生了,它首先是通过贤明的政治帝王的政治实践和生活实践具体体现出来的。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尧主要是作为一个光明磊落的政治帝王的形象出现的。他“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亲九族”、“合和万国”,将在自然社会中各分散的部落和民众集中在国家统一的领导之下。至于他所实行的禅让制度,后来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我认为,正是这个禅让制度,才可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真正的传统形式,世袭制倒是中国传统政治自我异化的产物。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将政治事业当做国家的集体事业而不是将国家视为自己家庭的私有财产的政治帝王,在十分自然的情况下都会将国家政权传承给自己认为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人,这个人在更多的情况下不会是自己的儿子或亲人。直至现在,我们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制度的进步,一直没有给予过十分恰当的说明。我认为,辛亥革命在政治制度方面带来的最大进步其实就是由世袭制重新恢复到了禅让制。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克服自身异化的结果,也是政治制度上的一个进步,但却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代替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那样的进步。从辛亥革命的这一结果也能充分地说明,禅让制很可能就是中国早期国家权力的传承形式。 舜实行的也是禅让制,他没有把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把政权交给了禹。但除此之外,在有关舜的传说中,还包含着中国古代国家及其政治帝王的更大量的信息。一个政治帝王拥有最大的权力,但这权力却只能用于国家的集体事业,而不能将其转换为个人的私产,这就要求他必须具备一般人所没有的品格。这种品格,不是在成为政治帝王之后才养成的,而必须是在没有任何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并且在拥有了权力之后也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以现在的观点,我们会认为舜的这种表现有点愚忠愚孝的性质,但要从衡量一个政治帝王的标准出发,我们就会感到,这恰恰是他能够成为一个贤明君主的最基础的条件。正是在这种逆境中,在这种完全被动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舜的坚韧,这不但是对自己生命的坚韧,同时也是对某种生活原则的坚韧。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论别人怎样对待我,我也不会离开正常的原则,将自己陷于不义的境地。这对于一个拥有无限大权力的政治帝王而言,不能不说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帝王只能有公仇,不能有私仇,他得是一个按照固定的原则待人接物的人,而不能是一个性好记仇、睚眦必报的人。否则他就会将国家的权力转化为个人的权力,陷入到私人恩怨的斗争中去。怯于公斗而勇于私斗的政治帝王,对于整个国家的破坏作用甚至更大于秦始皇一类的专制暴君。舜“耕历山,渔雷泽,作什器于寿丘”,并且每到一地,每做一事,都能受到人的拥护,都能把事情做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3]。这是一个负责的人,一个忠于自己职守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才能的人,一个能办实事的人,一个能够获得人的爱戴和尊敬的人。在成为政治帝王之前,舜还为尧臣多年,这样,舜作为一个贤明政治帝王的形象就得到了更全面的展示,他的为子、为人、为臣、为君,实际体现的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所必然要求于人、要求于一个政治帝王的。可以说,舜就是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活的标本。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将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就归结为舜文化,不是没有理由的。
3 p& }- g' `7 c. E | 
 /1
/1 